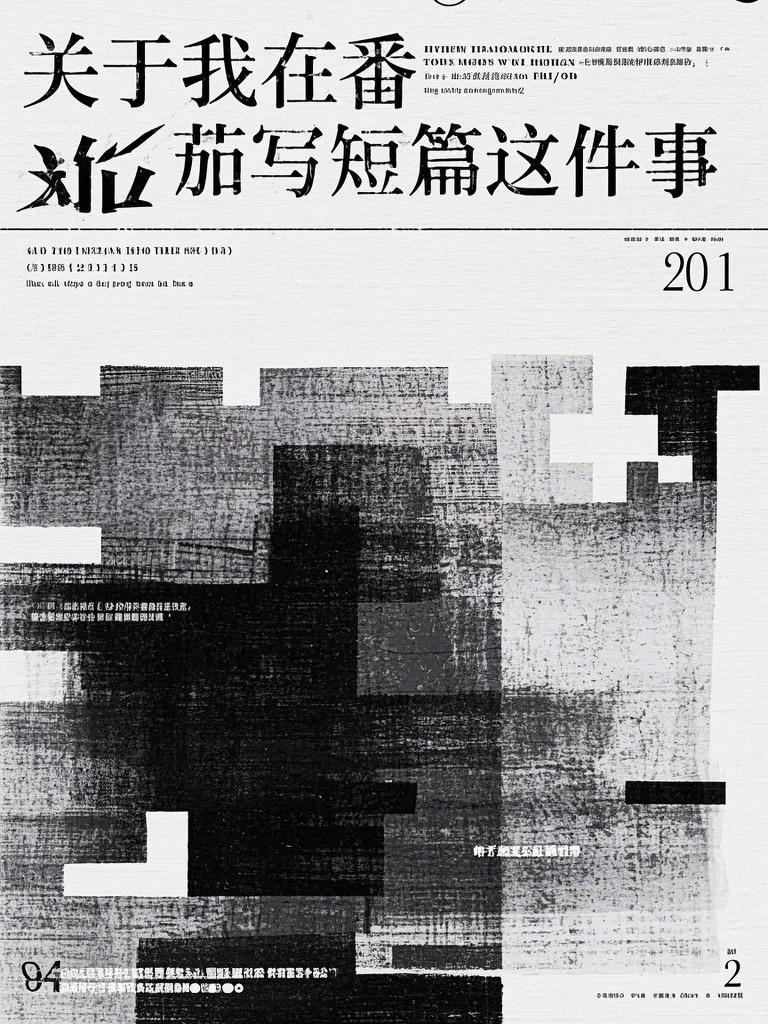“是。” 苏晚迎着他的目光,第一次没有躲闪,“我在傅先生这里,比在你身边自在多了。他知道我喜欢吃城南的生煎包,会让司机绕二十公里去买;他记得我对芒果过敏,所有甜品都换成了草莓味;他……”
“够了!” 凌曜嘶吼出声,周围的宾客纷纷侧目,“苏晚,你到底想要什么?我给你!我什么都给你!”
他突然单膝跪地,从口袋里掏出那个被捏变形的戒指盒,打开 —— 里面是一枚设计简约的钻戒,戒托内侧刻着 “曜 & 晚”。“我们结婚,好不好?” 他的声音带着恳求,像个无助的孩子,“我让凌氏注资苏氏,我去跟董事会抗争,我……”
“凌曜,你是不是傻?” 苏晚的声音陡然尖锐,带着刻意的嘲讽,“你觉得我现在还会稀罕你的求婚?你知道傅先生为了这场生日宴花了多少钱吗?你知道这条项链值多少个你手里的破戒指吗?”
她蹲下身,凑近他耳边,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声音说:“你连你妈给我的五百万分手费都不知道,还谈什么娶我?醒醒吧,你给不了我想要的。”
凌曜的瞳孔骤然收缩。五百万?分手费?原来她早就……
“我明白了。” 他慢慢站起身,脸上的血色褪得一干二净,眼神里的光彻底熄灭,只剩下死寂的灰烬。他看着苏晚脖子上的蓝宝石项链,忽然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苏晚,祝你生日快乐。”
说完,他转身就走,背影挺得笔直,却在走到宴会厅门口时,猛地踉跄了一下。
苏晚看着他消失的方向,指甲深深掐进掌心,血腥味在口腔里蔓延。傅景深递来一张纸巾:“演得很好,就是对自己太狠了。”
苏晚没接,只是望着那扇紧闭的门,声音轻得像叹息:“不狠点,他怎么会走。”
她不知道的是,凌曜并没有离开。他坐在车里,看着会所二楼露台上那个熟悉的身影,手里紧紧攥着那枚戒指,直到指腹被硌出血也没察觉。
雨不知何时下了起来,砸在车窗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他想起苏晚十八岁生日,他用攒了半年的零花钱买了条项链和蛋糕,在她家楼下等了三个小时,她冒雨跑下来,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上,却笑得比蛋糕上的奶油还甜。
那时的她,眼睛里有光。
而现在,那光灭了。
是他亲手掐灭的吗?
凌曜发动跑车,引擎发出暴躁的轰鸣,轮胎摩擦地面的声音刺耳。苏晚在露台上看到那辆熟悉的黑色宾利冲出去,猛地捂住嘴,才没让自己哭出声。
傅景深走到她身边,递给她一件披肩:“外面冷。”
苏晚没接,只是看着车影消失的方向,眼泪终于决堤。
她知道,从凌曜转身离开的那一刻起,有些东西就彻底碎了。像被暴雨冲刷的沙画,像摔在地上的琉璃,再也拼不回去了。
会所里的音乐还在继续,宾客们的笑声此起彼伏,香槟塔折射出虚假的繁华。苏晚站在这片喧嚣里,觉得自己像个被全世界遗弃的孤岛。
她抬手,摸了摸脖子上的蓝宝石项链,冰凉的触感穿透肌肤,直抵心脏。
凌曜,对不起。
等我。
可她不知道,有些等待,从一开始就注定了遥遥无期。
暴雨连下了三天三夜,像要把整座城市都淹没。
凌曜就站在苏晚家的别墅门口,任凭冰冷的雨水浇透全身。他已经在这里等了三天三夜,不吃不喝,眼底布满血丝,下巴上冒出了青色的胡茬,曾经挺拔的身影变得憔悴不堪。
别墅里没有开灯,像一座荒废的城堡。凌曜知道苏晚在里面,傅景深的车昨天就停在车库里,只是她一直没有露面。
他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是等她出来说一句 “我骗你的”,还是等自己彻底死心。可心底总有一个声音在叫嚣:她一定有苦衷,她那么爱你,怎么可能说变就变?
第四天凌晨,别墅的门终于开了。"

凌总,夫人带龙凤胎跑路了最新章节列表
推荐指数:10分
长篇霸道总裁《凌总,夫人带龙凤胎跑路了》,男女主角凌曜苏晚身边发生的故事精彩纷呈,非常值得一读,作者“兔捏”所著,主要讲述的是:苏氏千金苏晚曾是凌曜捧在手心的月光,一场家族破产,将她从云端拽入泥沼。为保父母周全,她含泪演了场“拜金劈腿”的戏码,转身投入商界大佬傅景深的羽翼下。凌曜的世界轰然崩塌,爱意淬成毒,恨了她整整七年。父母双亡的雨夜,醉酒的两人意外纠缠,苏晚带着破碎的心远走他乡,却不知腹中已悄然孕育两个生命。七年后,她以知名设计师“晚”的身份携龙凤胎归国,本想斩断过往,却与凌曜狭路相逢。他已是翻手为云的商界帝王,看着她身边酷似自己的孩子,妒火中烧,认定她早已嫁人生子,用最狠的手段处处刁难。设计稿被恶意泄露、合作方接连毁约、孩子生病时他冷眼旁观……苏晚筑起高墙,却在他笨拙的关心与失控的占有欲中逐渐动摇。当那本记录着真相的日记被揭开,凌曜才知自己恨错了七年,疼错了七年。“晚晚,我把命给你,能不能再爱我一次?”他跪在她面前,捧着用七年悔恨换来的真心,而她看着两个懵懂的孩子,终究要在爱恨的废墟上,决定是否拾起那缕烬余的温暖。...
第11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