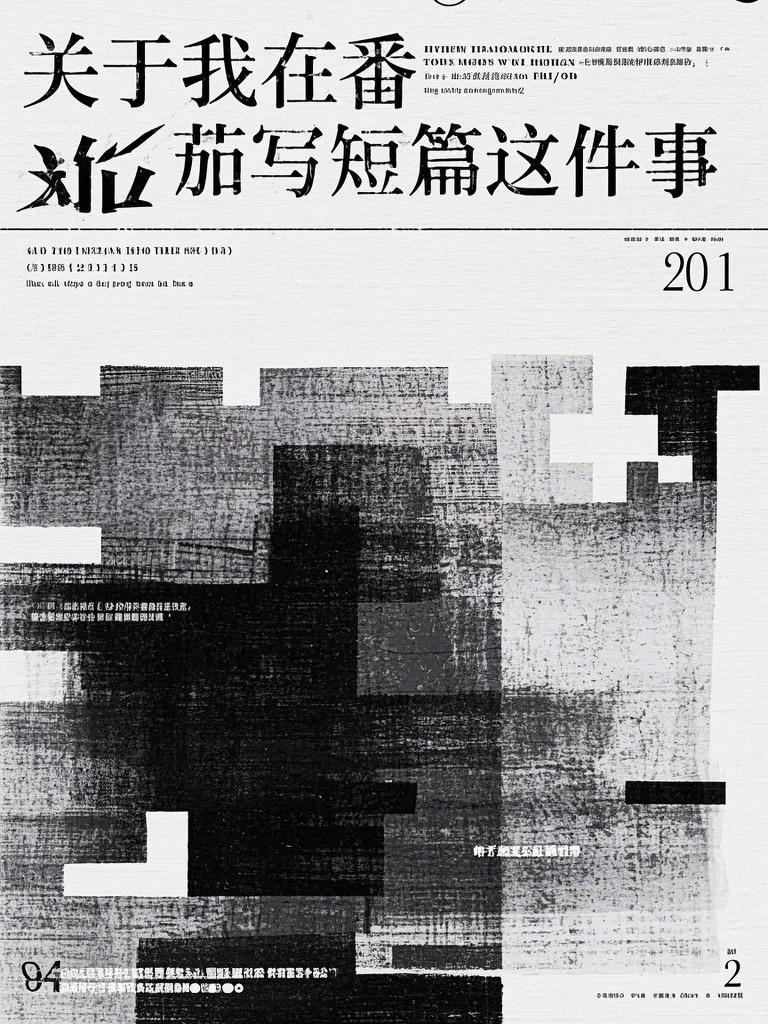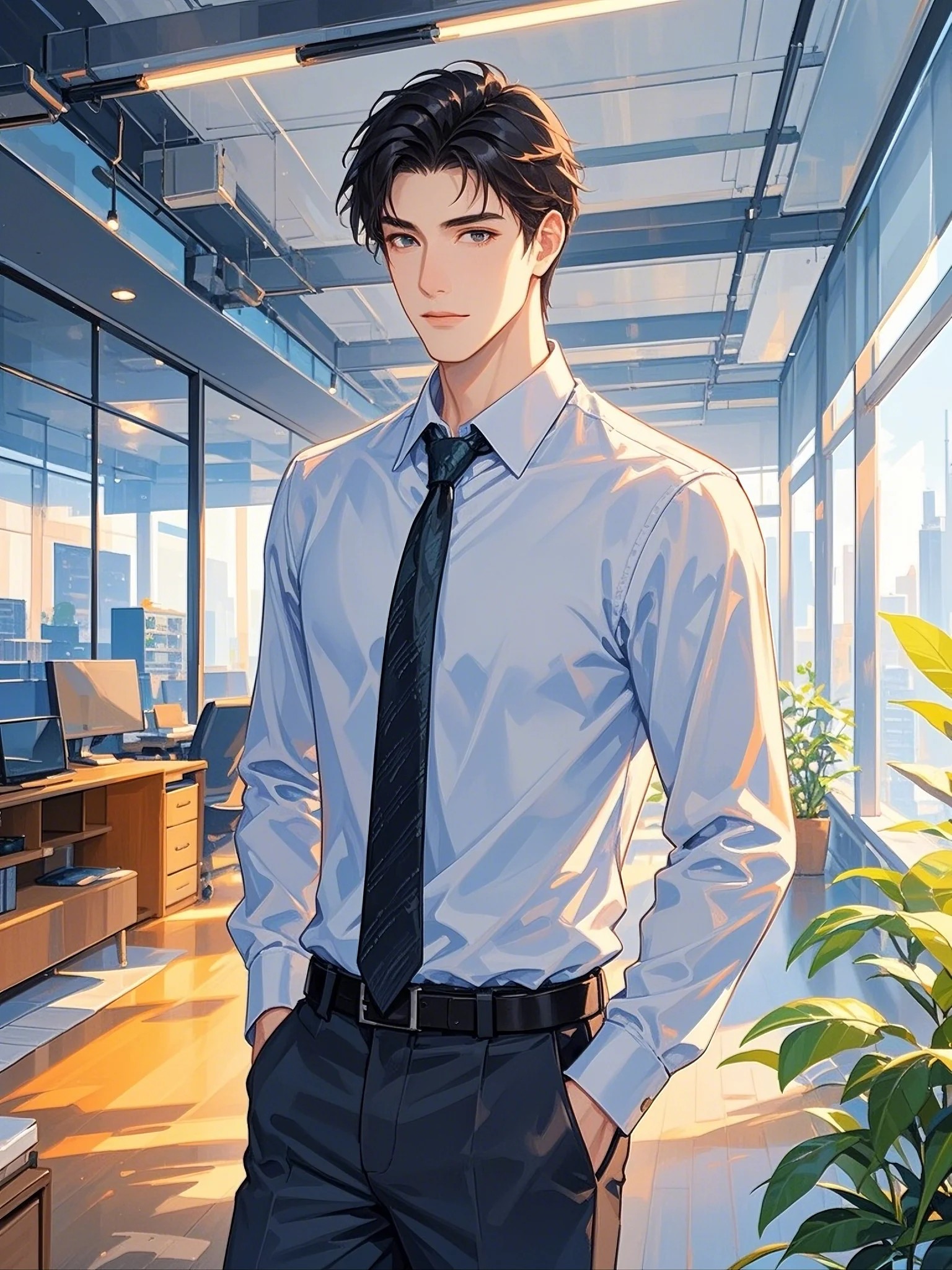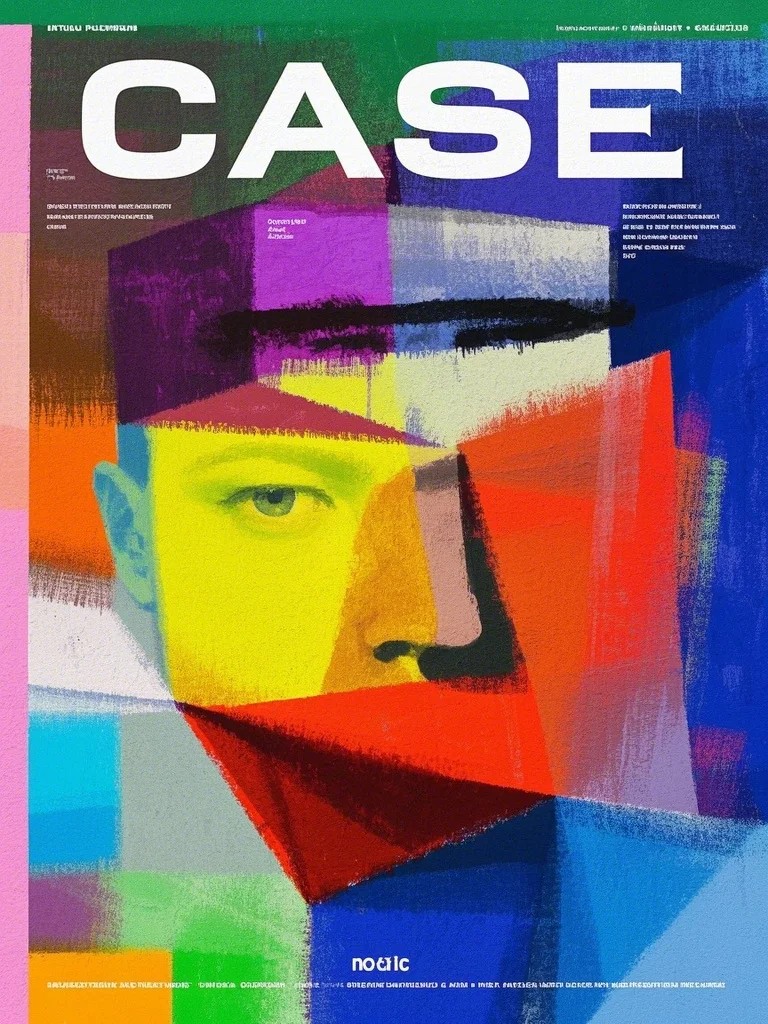—
苏砚抬眼看他,眼中无怒,只有冷静。
他沉声开口:
“若照使君所言,唯籍为尊,唯位为先,唯制为法。”
“则先问——若民有急,官不言,席不闻,是守礼,还是弃政?”
他转头望向堂中众吏:
“诸位——敢说,这些年来,策堂所问一策无实、策席无功、问者无德么?”
沈墨微抬下颔,虞和拱手道:“问策三题,民有其益。”
潘师叹息,却也朗声开口:“席虽未定,问则有功。”
堂中数十名议员先后起立,虽语调不高,但气势渐起:
“三问,非毁一人,是毁策堂。”
“若王廷弃问,民必寒心。”
—
苏启微微皱眉,却未变色。
他掏出最后一物——一卷黄绢玉册。
上书:
“齐廷官印录:苏忱,病故,尸返即墨。其名,非苏砚。”
他淡声道:“你之名,未入齐档,今入魏署,可否——自证?”
此刻,全堂目光,再次落于苏砚身上。
苏砚静立不语,忽而朗声说道:
“我,苏砚。”
“不凭名,不凭位,只凭我所答——五策之问。”
“若三月之内,所策不能解五问,废我无妨。”
他高举策简:
“若五问得解,还请王廷自封一席。”
沈墨霍然起身,朗声道:
“东宫应允——三月之问,不定其名,只定其策。”
齐使沉吟半刻,终于点头:
“准。”
“三月之后,吾再来问你。”
⸻
齐使之问落定,三月之限已定。
但堂外的风,并未因此而止。
沈墨离堂后,回至东宫偏厅,言语不多,只命虞和留意律院动向。潘师则亲自送信至“问议坊”,要求暂封三日,甄别策题。
而在策署西阁,庾济与章原一行人密谈已久。
烛火之下,一张新拟的议草被缓缓展开——
废策三纲 · 外传修订本
1. 策席无职,不得问政;
2. 策文涉兵,不得列堂;
3. 策吏无籍,不得定章。
这三条一旦落印,不动苏砚一人,却能彻底断绝“民问政事”之路。
章原盯着那份草案:“此章一出,苏砚纵使三问再成,也无人敢接。”
庾济却只淡淡道:“不够。”
“你知他在做什么吗?”
“他在将策堂之问,从‘内问’引向‘外问’。”
“若不封他,他便能把策堂变为‘共策之堂’。”
“到那时——便不是废一人之席,而是王廷一半吏制都将重写。”
章原沉默良久,低声道:“那便不只是废他。”
“是让他自己写下‘策问不成’。”
—
此时,苏砚已展开第一策问案:
错编役籍案 · 初议简
案目:南市十六役籍错编,三年无改,五人枉死,役籍补文有伪改之嫌。
所涉机构:役署、宗正署、仓议司。
所涉官员:名讳隐去,待查证后公示。
所引法章:魏律·役籍编审令第三条,役名错录三月不报,属官连坐一等。
所提疑问:
• 当年役册为何未由主簿签押?
• 代笔吏“卿同”书录为何以役名口述为准?
• 是否有“上级授意删换”之嫌?
苏砚将此案贴于问策堂侧,向民众开放查阅与问写反馈。
问议坊于三日内收到回应四十余封,多数指向——
“旧年役籍对查时,仓吏私收三两银钱可换顺序。”
“未到役年者,若通粮府之人,可推三年之后。”
“某役名户已故,实由旁支代名服役。”
潘师看后皱眉道:“这不是错名,是养名、借名、卖名。”
“这是‘名籍经济’。”
苏砚道:“所以我写这一问,是要从‘错名’入手,查出‘谁在贩名’。”
—
就在这时,虞和带来律院传讯。
策署议草·再审通告:
因“策案有涉律政权责争议”,律院将召集三署、问堂策官,于三日后集议“策政权责边界”。
潘师一见此文,脸色当即沉下:“来了。”
苏砚一眼看完:“他们要立章。”
“废策三纲,要被塞进这‘集议’里。”

战国谋主,我于乱世布天局前文+后续
推荐指数:10分
军事历史《战国谋主,我于乱世布天局前文+后续》是由作者“写书是自愿的”创作编写,书中主人公是苏砚齐王,其中内容简介:他本是籍籍无名的书生,一朝穿越,魂落战国,成为齐国弃子,被幽禁魏国江阳郡,病榻待死。苟延残喘之间,他以一纸仓券搅动郡府风云,以一身算计扭转命运棋局。朝堂阴诡,人心如镜,质子、弃子、乱世孤子,他步步为营、谋中藏谋,誓要从局中人,翻作布局者!局从江阳起,棋落诸侯间。敌人不蠢,权臣不傻,反派不跪,情感不水。弱国质子,也能掀起万里风雷!...
第36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