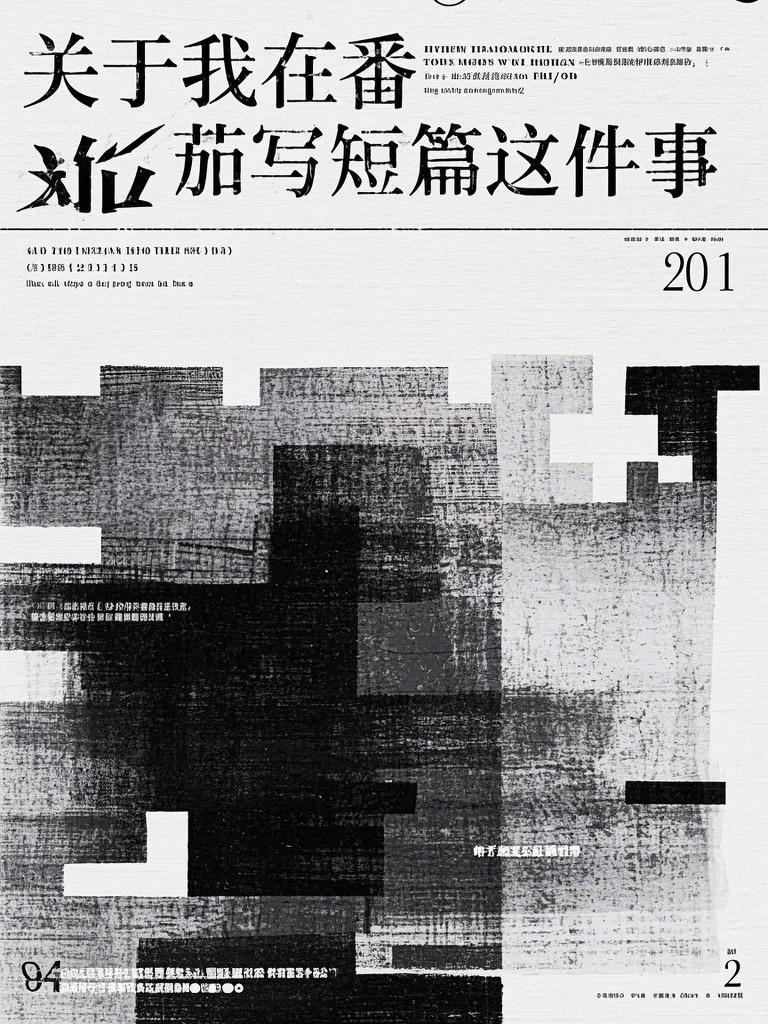厅内顿时一片死寂。
"这...这..."武定侯郭培民声音发颤,"这...这刘泽清...原想着好歹是个手握兵权的,若能攀上关系..."
他突然抓住张之极的衣袖,指节都泛了白:"国公爷!皇上前脚刚抄了成国公,定国公府,后脚就砍了刘泽清的脑袋,咱们可就剩下您这一个主心骨了,后面若是皇帝拿咱们开刀可如何是好啊!"
"国公爷!您可得给咱们拿个主意啊!"阳武侯薛濂"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额头上的汗珠在烛光下闪闪发亮,"我薛家世代忠良,可不能就这么..."
泰宁侯陈延祚也接上:"是啊国公爷!您在皇上面前说得上话,求您给指条明路吧!我陈家上下百余口的性命..."
襄城伯李国桢还算镇定,但脸色也已煞白。他上前一步,压低声音道:"国公爷,咱们这些勋贵可就剩您这根顶梁柱了。皇上若是真要赶尽杀绝..."他说着瞥了眼门外,声音又低了几分:"是不是该早做...打算?"
新乐侯刘文炳突然拍案而起:"要我说,不如..."话未说完,就被张之极一个凌厉的眼神制止。
"都给我住口!"张之极一声暴喝
众人面面相觑,大厅内再次寂静。
张之极率先看向李国桢说道:“李国桢,你以为陛下让孙传庭整顿京营把你给漏掉了吗?倒卖军粮军需,占役,吃空饷,练兵无能、治军无方。你以为这些陛下都不知道吗?”
随即又看向众人大声喝道:“你们哪个敢说自己高风亮节、克己奉公的?哪个家里没有上万亩强占的民田?地窖里没有几十万贪腐的银子?贿赂官员,无视律法,草菅人命,你们真以为皇上是睁眼瞎?
张之极越说越怒,额头上青筋暴起。他猛地转身,一把抓起桌子上的茶杯,狠狠砸向墙壁。“哗啦”一声,茶杯瞬间粉身碎骨,碎片溅落在地。
他大步走到窗边,双手用力拍打着窗台,木质的窗台被拍得“砰砰”作响。“平日里只知道贪图享乐、中饱私囊,全然不顾国家社稷!如今大祸临头,却只知道哭天喊地求主意!”
屋内几人被张之极喷的狗血淋头,各个都低着头向被霜打的茄子。
张之极目光扫过众人惨白的脸色,见时机已到,突然压低声音道:"诸位若想活命,眼下唯有一条生路——"
众人闻言,瞬间来了精神,纷纷抬起头七嘴八舌的追问。
"国公爷!有什么法子您快说啊!"
"是啊!"这都什么时候了,您就别卖关子了!"
"国公爷,只要能让全家老小活命,让我做什么都成!"
张之极环顾众人,缓缓道:“主动请罪,将这些年贪腐所得尽数上缴国库,再献上自家田产,为朝廷分忧。”
众人一听,脸色更加难看。
张之极冷笑一声:“你们是想保住这些身外之物,还是想保住全家老小的性命?陛下如今已对咱们起了杀心,若不主动请罪,等陛下动手,怕是连祖坟都要被刨了。”
厅内顿时骚动,屋内的众人开始三三两两的商议起来,
张之极话锋一转:“你们可知皇上抄了朱纯臣、徐允桢却为何偏偏留下我张之极?”
勋贵们面面相觑
“因为我已经献出全部家产给陛下,陛下给我交了底,主动献出九成家产以充国库,过往种种,既往不咎。并且爵位可保!"
阳武侯薛濂闻言,手中茶盏"啪"地落地粉碎:"九...九成?!"
"嫌多?"张之极冷笑一声,突然拍案暴喝:"那便等着锦衣卫来抄个十成!到时候你们挨个跪在诏狱里等着砍头那会儿可别来求我!"
勋贵们闻言,顿时如遭雷击。"

明史看到一半,我穿成了崇祯帝!人气小说
推荐指数:10分
古代言情《明史看到一半,我穿成了崇祯帝!》是由作者“流于你心”创作编写,书中主人公是崇祯王朴,其中内容简介:我是历史系研究生,周末在图书馆看明史时,被炸雷劈到穿越成崇祯帝。睁眼就在紫禁城东暖阁,老太监哭着喊皇爷,太医说我受惊吓气血不畅。得知此刻是崇祯14年松山大战时,大明危如累卵。我深知责任重大,强压震撼,模仿帝王口吻安抚众人,从此刻,我要以崇祯身份,力挽狂澜救大明。...
第46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