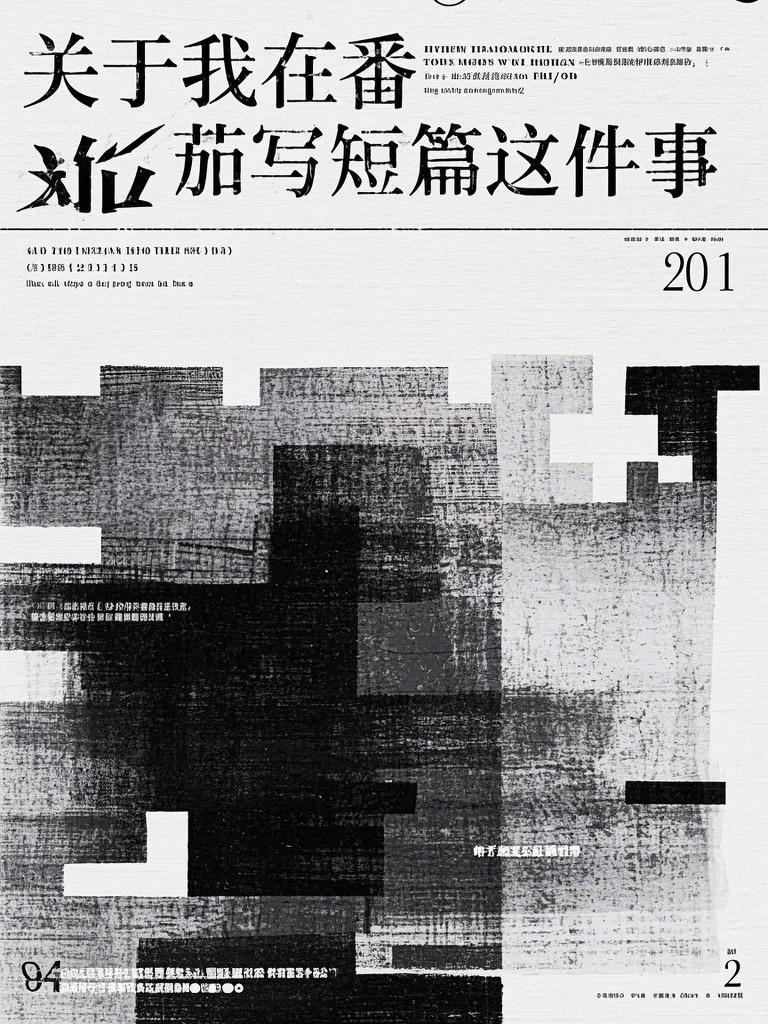真不是他敏感肌,他是真觉得段承霄有点奇怪,似乎是对幺幺有点过分的偏向,又是放水又是给台阶又是送衣服又是夸人家漂亮的...
这还是他看到的,没看到的...
程冶原本是有点愁的,但细想之后又觉得有点好磕。
抿着的嘴角渐渐上扬。
但这两个人认识都没多久,看段承霄这样子,多半也是觉得人家好看,一时间有点上头。
一定是上头而已,程冶执着的这样想着。
-
次日。
程冶一起来就看到段承霄站在院子里。
这兹县虽然说没那么繁华,但好在节奏慢,生活悠然,早上起来浇浇花养养鱼什么的很不错。
就像此时段承霄站在院子里,一手拿着手机在打电话,一手拿着水管在浇花。
程冶放轻了脚步,拉了条玻璃门的小缝,身子靠在门边眼睛贼兮兮的看着门外打电话的段承霄。
不知道是谁打来的电话,但听着感觉他语气不是很好。
说着话,手上的浇花的动作就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寿辰我会去,回家就不必了,不是您说的吗?让我磨练心性。”
“他母子俩算盘打得都蹦我脸上了我还回去?我是什么很贱的人吗?”
“您老婆说的,贱人生的贱种,那我的确挺贱的。”
他说着,自己都笑出声来,
程冶一听就知道这是在和他老子说话,每次都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地步。
之前他那后妈装作对他挺好的,当时他说话还客客气气的,自从被坑了之后那母子俩就撕开了假面。
程冶当时还记得去找段承霄的时候他在家里是怎么舌战群儒的。
甚至在来兹县的前一天还把那后妈骂进了医院。
那时候程冶说他疯了,段承霄嗤笑一声:“你就当我是疯了吧,反正离疯也不远了。”
那时候看着段承霄,程冶总觉得他的变化不仅仅只是苏杳害他丢了继承人这件事,他大概是还知道了别的事情,才会那样不顾一切的无差别攻击。
想到这里,程冶又往外贴了贴,想再听听他说的什么。
却只见段承霄漫不经心的双手拿着水管摆弄,手机被夹在脸颊和肩膀的缝隙里。
他低着头研究着手里忽然断流的水管,一回头就看到某个鬼鬼祟祟的人贴着墙面踩着他的水管。
段承霄嘴角抽了抽,随手挂了电话,看着程冶指了指自己手里的水管。
一脸沉默。"

扶腰直上抖音
推荐指数:10分
小说《扶腰直上》,超级好看的现代言情,主角是乔芮苏杳,是著名作者“呆头梨”打造的,故事梗概:【先婚后爱联姻暧昧拉扯双C】【明艳性感千金伪纨绔阔少】被逼联姻后苏杳找了个小地方躲起来,日子过的逍遥自在。第一次见段承霄是在酒吧,他倚在吧台边,她多看了两眼,身旁的朋友打趣道:“看上了?那是老板。”苏杳轻笑,没想到能在这儿看到那结婚证上从未见过面的老公。她心里谋算着,朝他那儿走去,起身时身影晃动,走下楼梯时腰间被人轻扶。苏杳侧眸,眼神迷离间道了声谢。一时兴起的苏杳原本只是想逗逗他,后来又心生利用。却未曾想她虚情假意的利用和勾搭把自己搭了进去。-段承霄以为自己出轨了,不受控制的对另一个女人心动。知道苏杳对他诓骗隐瞒后更是又气又恨。气她不早说白白看他这么久笑话。恨他自己没出息,对她甘之如饴-我愿做你的登云梯,送你扶摇直上九万里。...
第33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