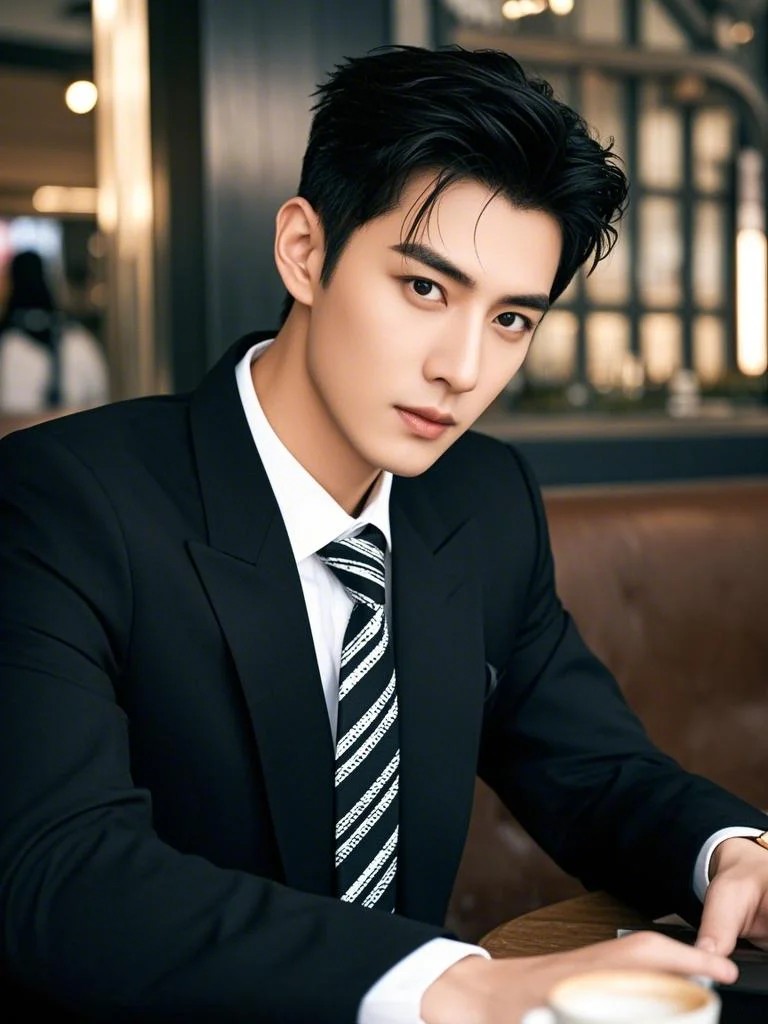崇祯目光微转,看向侍立殿侧的锦衣卫千户高文采与王国兴,指尖在龙案上轻轻一叩。霎时间,殿外传来整齐的脚步声,数百锦衣卫力士鱼贯而入。
"带诸位大人去北镇抚司...好生记录供词。"
高文采与王国兴对视一眼,同时抱拳应诺。
晨曦初现时,数百名朝臣踏着晨露入宫,朱紫袍服映得奉天门一片辉煌;待到日上三竿散朝时,却只剩寥寥几十人踽踽独行,空荡的御道上投下几道伶仃的影子。
下朝后崇祯回到了东暖阁,不禁在心中盘算:“算时辰,此刻清河大营那边应该已经接近尾声了。”
正负手在暖阁内踱步。忽听门外传来细碎的脚步声,王承恩躬身入内,拂尘一甩跪倒在地。
"皇爷,"老太监声音里带着几分喜气,"老奴已在清河大营当众宣旨。那些兵丁们听得补发历年欠饷,无不感激,个个跪地高呼万岁。"他略直了直身子,"孙大人和黄大人亲自盯着发饷绝无差错。"
崇祯听完奏报,神色未动,只是指尖在军报上轻叩三下:"拟旨。"声音如古井无波。
王承恩连忙捧来笔墨,只见皇帝提笔蘸墨,在明黄绢帛上挥毫:
"敕封黄得功为山东总兵,赐虎符,即日赴任。至山东后——"持笔的手突然一顿,
"第一,查抄刘泽清府邸,所获赃银尽数犒赏山东留守将士;第二,拨发土豆、番薯各一千石,命其亲自督导推广。"
合上册页时,他又补了一句:"另,清河降卒两万暂编入京营,由孙传庭统一操练。"说完将圣旨递给王承恩,目光却投向窗外。
现在已经十月份了,留给他的整备时间只剩下不足一月。
他眉头一皱凝视着案头堆积的奏章,指尖轻叩着空置的官缺名录。今日这场"大清洗"虽充盈了国库,却也让六部衙门空了近半,剩余的官员也都是人心惶惶。
王承恩躬身应道:"老奴遵旨。"正欲退出,崇祯却突然说道:“等等!”
说着,又拿起纸笔匆匆写了一封密信,一并递给了王承恩。
"把这个也带去给黄得功,再告诉他,朕准他在山东便宜行事,务必速战速决。"
"老奴明白。"王承恩恭敬应答,缓缓退出了东暖阁。
崇祯在王承恩走后,出了东暖阁,在这偌大的皇宫内转了起来,一边逛一边消化这些天发生的事情。
眼下,诛杀刘泽清后,孙传庭必须要出兵,还必须要胜!
因为现在大明的军阀不止刘泽清一个,还有湖广的左良玉,拥兵二十余万,陕西一带的高杰,拥兵四万。这些人基本上都处于听调不听宣的状态。
启用孙传庭,诛杀刘泽清,抄家勋贵权臣,这种种行为都代表朝廷要收兵权。此刻天下军阀想必都在暗自揣度:"陛下既敢动刘泽清,下一个...会不会就是我?"
刘泽清一死这些军阀们必定兔死狐悲,消极观望,甚至可能联合起来对抗朝廷。
洪承畴大军被围,若坐视不理,则辽东防御体系全线奔溃,各路军阀将更不会把朝廷放在眼里。现在刚收的山东兵要驻防京城,黄得功的三万人马在守安徽,能调动的就只有孙传庭新练的两万人了.....
"此战..."崇祯的手微微发颤,"若胜,则昭示着朝廷仍有重整河山之力;若是败,建奴就会大举入关劫掠,导致人心尽失,朝廷也无与其一战之力。而那些军阀们,不是屈膝跪迎李自成的闯旗,便是剃发易服,匍匐在建奴的马蹄之下。
他望向辽东方向。一阵秋风卷着枯叶掠过紫禁城的红瓦。
"此战若败...这巍巍宫阙,终将沦为建奴跑马场。"
眼前仿佛浮现出史书所载的惨状: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八十一日...秦淮河水赤,江南骨如山。八旗铁骑所过之处,剃发令下,汉家衣冠尽毁;圈地令出,北方百姓皆成奴隶。
而自己这个皇帝又能怎么样呢?只能逃往南京,或提前学历史上的崇祯帝找一颗歪脖子树吊死。"

明史看到一半,我穿成了崇祯帝!全新
推荐指数:10分
正在连载中的古代言情《明史看到一半,我穿成了崇祯帝!》,热血十足!主人公分别是崇祯王朴,由大神作者“流于你心”精心所写,故事精彩内容讲述的是:我是历史系研究生,周末在图书馆看明史时,被炸雷劈到穿越成崇祯帝。睁眼就在紫禁城东暖阁,老太监哭着喊皇爷,太医说我受惊吓气血不畅。得知此刻是崇祯14年松山大战时,大明危如累卵。我深知责任重大,强压震撼,模仿帝王口吻安抚众人,从此刻,我要以崇祯身份,力挽狂澜救大明。...
第52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