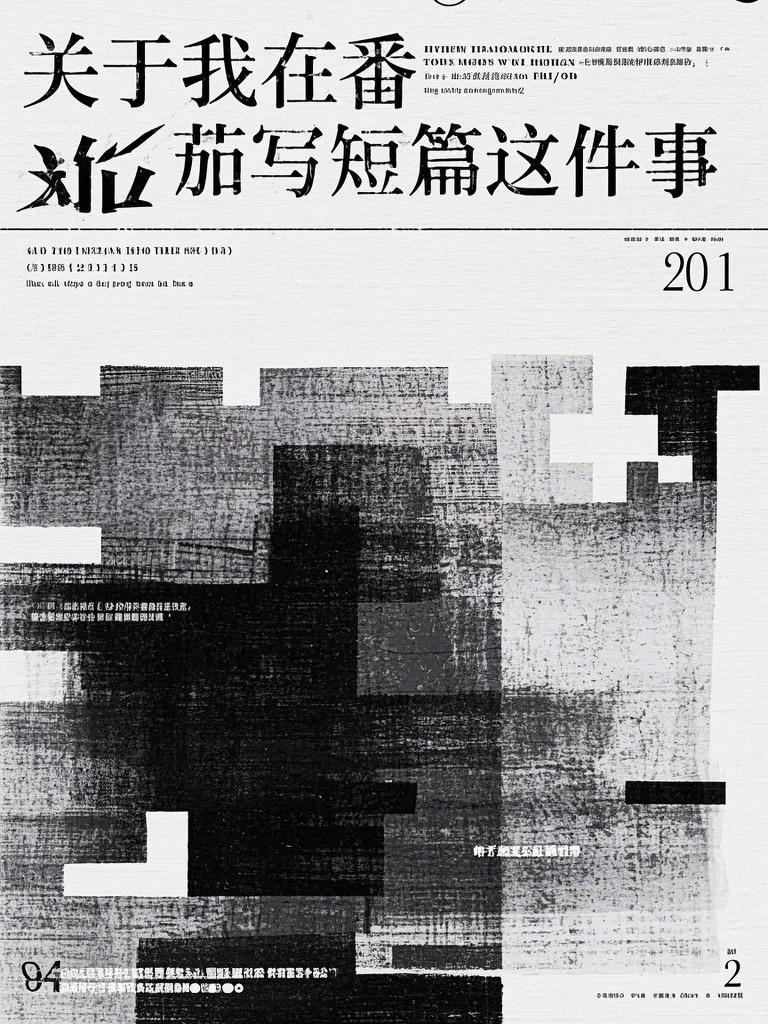薛蘅艰难地抬起下颌,目光却依旧不敢直视萧母的眼睛,她谦卑地回应:“老夫人,婢妾定会谨记,恪守本分,绝不敢有丝毫非分之想!”
“罢了。谅你也不敢。记住今日的话便好。珂儿,我有事先行一步,你且留在这里,接薛氏的茶。”萧母留下一句,便带着侍女离开。
宇文珂欠身行礼,姿态无可挑剔,“是,母亲慢走。”
薛蘅继续屈膝下跪,给宇文珂敬茶:“夫人,请喝茶。”
宇文珂不愿为难她,直接接过茶水喝了一口。只是当她看着薛蘅眼中无法掩饰的悲愤、绝望和那深埋的恨意,宇文珂脸上那温和的笑容淡了些许。
“我知你心中不甘,知你恨意难平。”宇文珂的声音压得更低,“你的来历,你的苦楚,包括…那个孩子,我都知晓。”
薛蘅的心猛地一沉,聿哥儿,她突然提到此事,究竟为何?
“我成婚那日,他未入我房中,让我一人独守空房。”她漠然地陈述着事实,“他去了哪里,想必你现在也明白了。”
原来…原来他是在自己大婚之夜抛下新娘,千里奔袭去抓她这个逃跑的“猎物”?可她未曾从宇文珂言语中,发觉出一丝的抱怨。
“这世道,对女子何曾真正公平过,你恨他将你强掳至此,恨他逼迫你们母子,这恨得确实有理。可只是恨,又能让他如何?”
她的目光锐利地刺向薛蘅:“你今日还能跪在这里奉茶,还能站在我面前,不是因为你认命了,而是因为你不敢不认命。为了那个孩子,你什么都愿意认,不是吗?”
宇文珂看着温婉可人,可说出的话却冰冷地戳破了她所有的伪装。是的,为了聿哥儿,她什么屈辱都能咽下。
“殿下的性子,你领教过了。”宇文珂放下茶盏,“刚极易折。你与他硬碰硬,无异于以卵击石。结果,只会是你粉身碎骨,连带着你唯一珍视的那个孩子…一起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宇文珂言语中带着冷酷的清醒:“我与他之间的婚姻,是权力的交换。而你,沈氏,你已是他的人,腹中怀着他的骨肉。这是你的命,也是你儿子的护身符。”
就在这令人窒息的绝望中,薛蘅的目光无意识地掠过宇文珂近在咫尺的脸庞。那温婉的眉眼,那挺秀的鼻梁……脑海中,一幅模糊的画面如同闪电般转瞬即逝!那似乎是很多年前,一个同样寒冷的冬日…
她骤然抬头,几乎忘记了尊卑礼数,直截了当地询问:“夫人,你为何如此…说句冒昧的话,婢妾好似在哪儿见过你。”
宇文珂迅速垂下眼睫,长长的睫毛在眼下投下一小片阴影,完美地遮掩了那一瞬间的失态。她也是这几日才认出薛蘅竟是故人,只是如今不可让她知晓身份。
宇文珂她微微倾身,靠近薛蘅:“你我…也算是有缘,只是往事如烟,不必深究,更不必再提。今日我看在故人的份上,助你一把。你要记着,活着,才有念想,才有…逃离的希望。”最后两个字,她说得极轻。
薛蘅浑身剧震!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逃离?这位郡王妃,这位刚刚还在劝她认命、警告她不要对抗的正妻,竟然对她说……“逃离”?!
说完,宇文珂直起身,脸上又恢复了那种端庄温和的笑意,随即拿起一支成色极好的玉簪,递向薛蘅:“这簪子,算是我给你的见面礼。以后安分守己,尽心伺候殿下,为郡王府开枝散叶。”
薛蘅麻木地伸出手,接过那支冰冷的玉簪。为了聿哥儿,她必须认下这屈辱的命运,必须咽下这滔天的恨意,在这狼窝里,像一株藤蔓般依附那个毁了她一切的男人,苟且偷生。
屋内响起嬷嬷宣布礼成的声音,薛蘅只觉得眼前发黑,耳边嗡嗡作响。她攥紧了手中的玉簪,尖锐的簪尾刺破了掌心,一丝微痛传来,却远不及心口的万分之一。
这场荒诞的纳妾礼结束了。她不再是那个路过炎州、一心只想带着儿子回亡夫故里的中原妇人薛蘅。她是萧铎的妾,是老夫人眼中需要敲打和防备的祸水,是宇文珂口中必须“认命”的棋子,是为了聿哥儿必须活下去的行尸走肉,是陇南郡王府里的侍妾“薛娘子”。
“逃离…”,“忍耐”,“静待时机”,薛蘅在心中默念着…
日影西斜,竹影摇晃。
前些日子,薛蘅暗中托付刘婶拿着她绣的双面绣花样,到绣坊贩卖。
本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曾想竟得到掌柜的青睐,掌柜对薛蘅的手艺赞不绝口,当下便跟她约定,日后定期交付成品。
这意外的机遇,让薛蘅满怀憧憬,若是能靠着这门手艺好好攒点钱,往后若是能跟聿哥儿逃离大梁,也好有安身立命之本。
“吱呀”,一阵突兀而刺耳的开门声传来,薛蘅身体微不可察地绷紧,手中的银针险些刺破指尖。她猛地抬起头,目光警惕地望向门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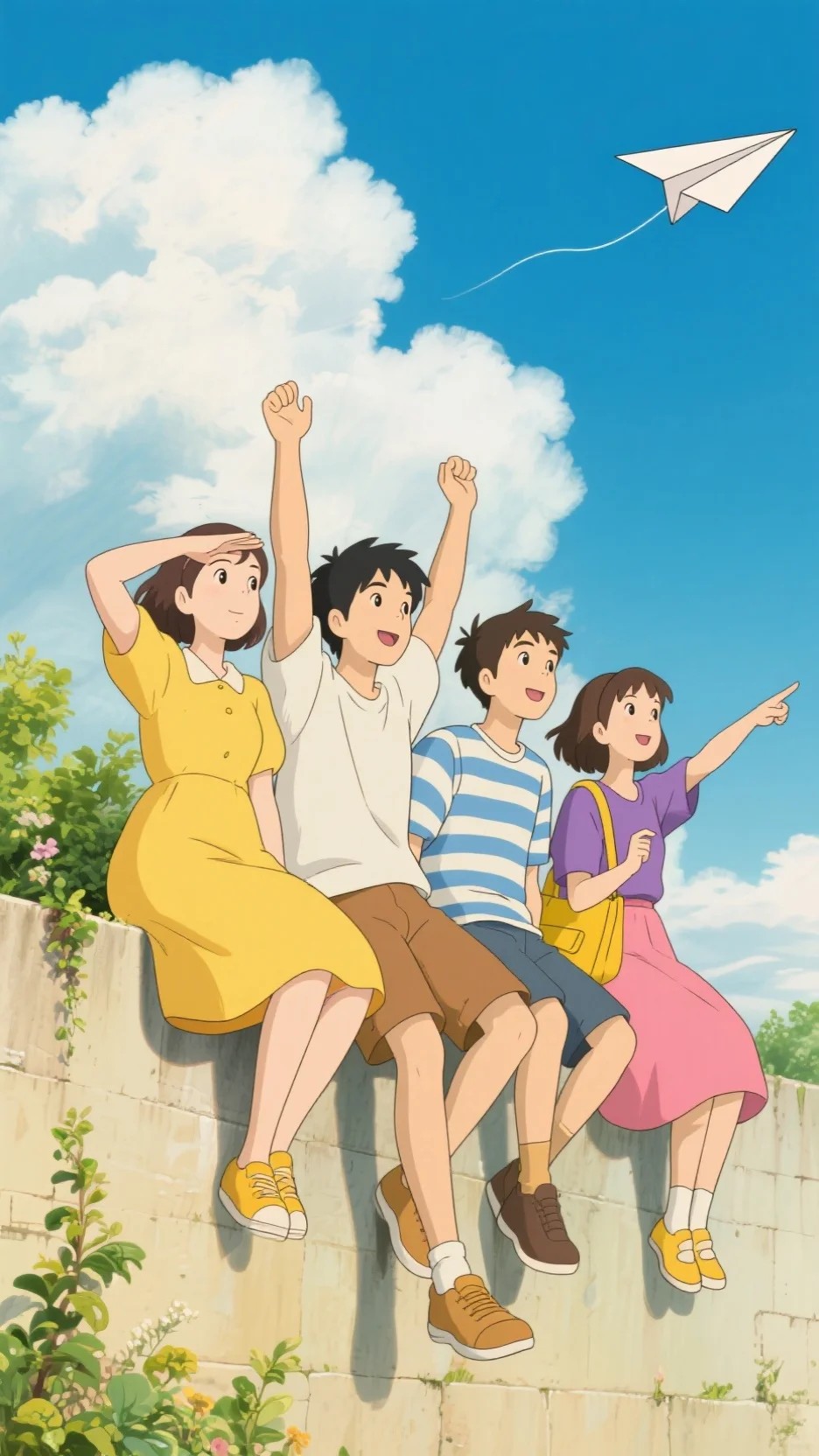
金屋囚娇:强夺中原美人最新章节列表
推荐指数:10分
现代言情《金屋囚娇:强夺中原美人》目前已经全面完结,萧铎薛蘅之间的故事十分好看,作者“淡淡的橘猫”创作的主要内容有:【体型差➕强取豪夺➕带球跑➕破镜重圆➕女非男c】【艳绝江南、善于刺绣的中原女主Vs强势霸道、权势滔天的鲜卑男主Vs青梅竹马、温润如玉的皇商男二】江南烟雨养出的温婉妇人薛蘅,携幼子北上寻夫,孤身踏上边疆险途。初见时,女子发髻凌乱,粉唇饱满,胸脯处的领口略微破碎,若隐若现的春光,勾得萧铎心神大乱,一时失了魂。再见时,他压着薛蘅,说着纯正的汉话,满是讥讽:“薛夫人何故如此扭扭捏捏,如此不洁之身,这般做作又是给谁看?”----几年后,萧铎跪在青石板上,任由暴雨冲刷他身后泛着血的鞭痕,满身狼狈:“阿蘅!别走,别丢下我一个人!”薛蘅却将热茶泼在他脸上,字字如冰:“你是何人?也配让我停留?”说着,直接将萧铎强塞给她的定情信物扔在地上,碎成两半,头也不回地走了。...
第45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