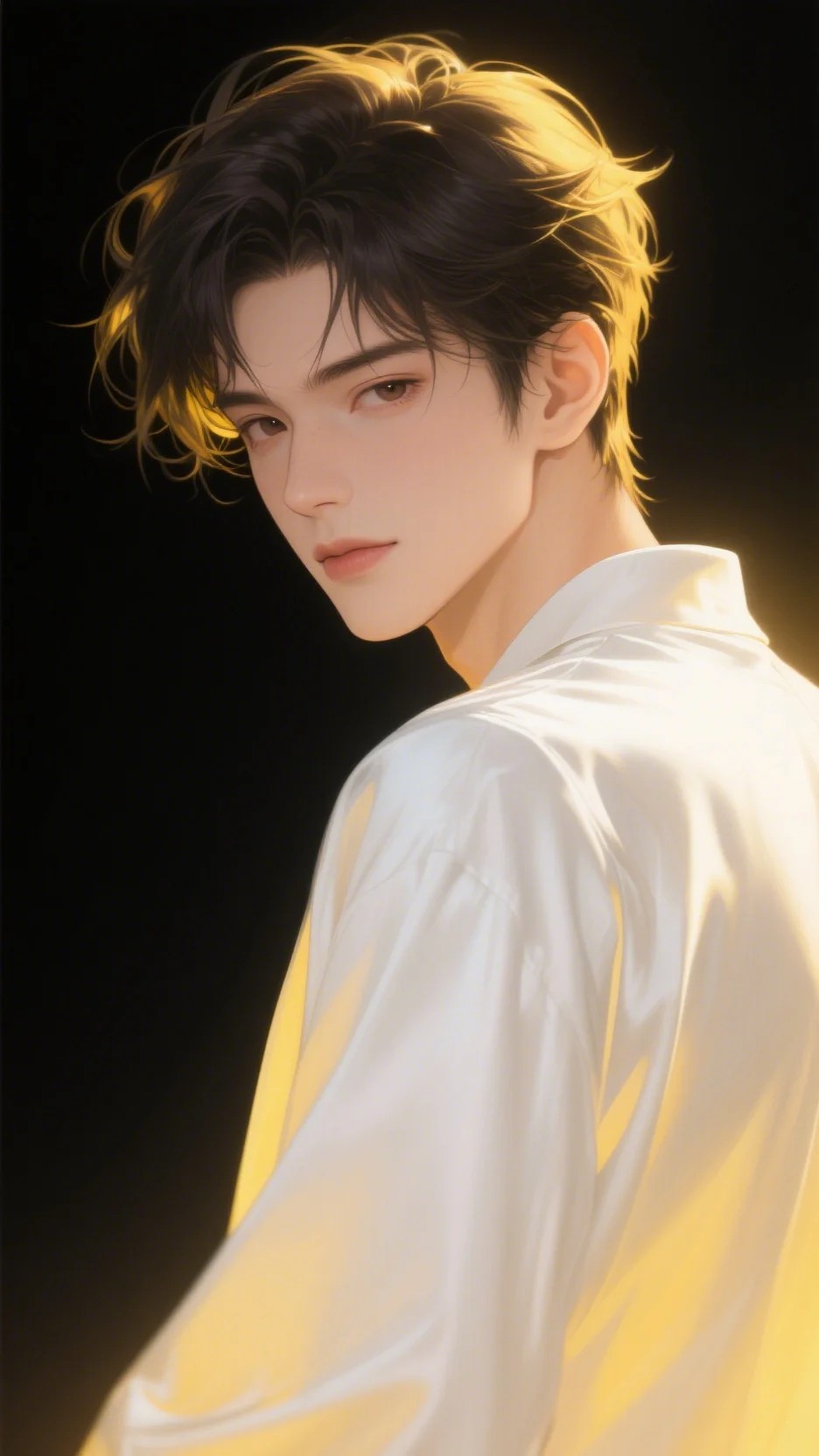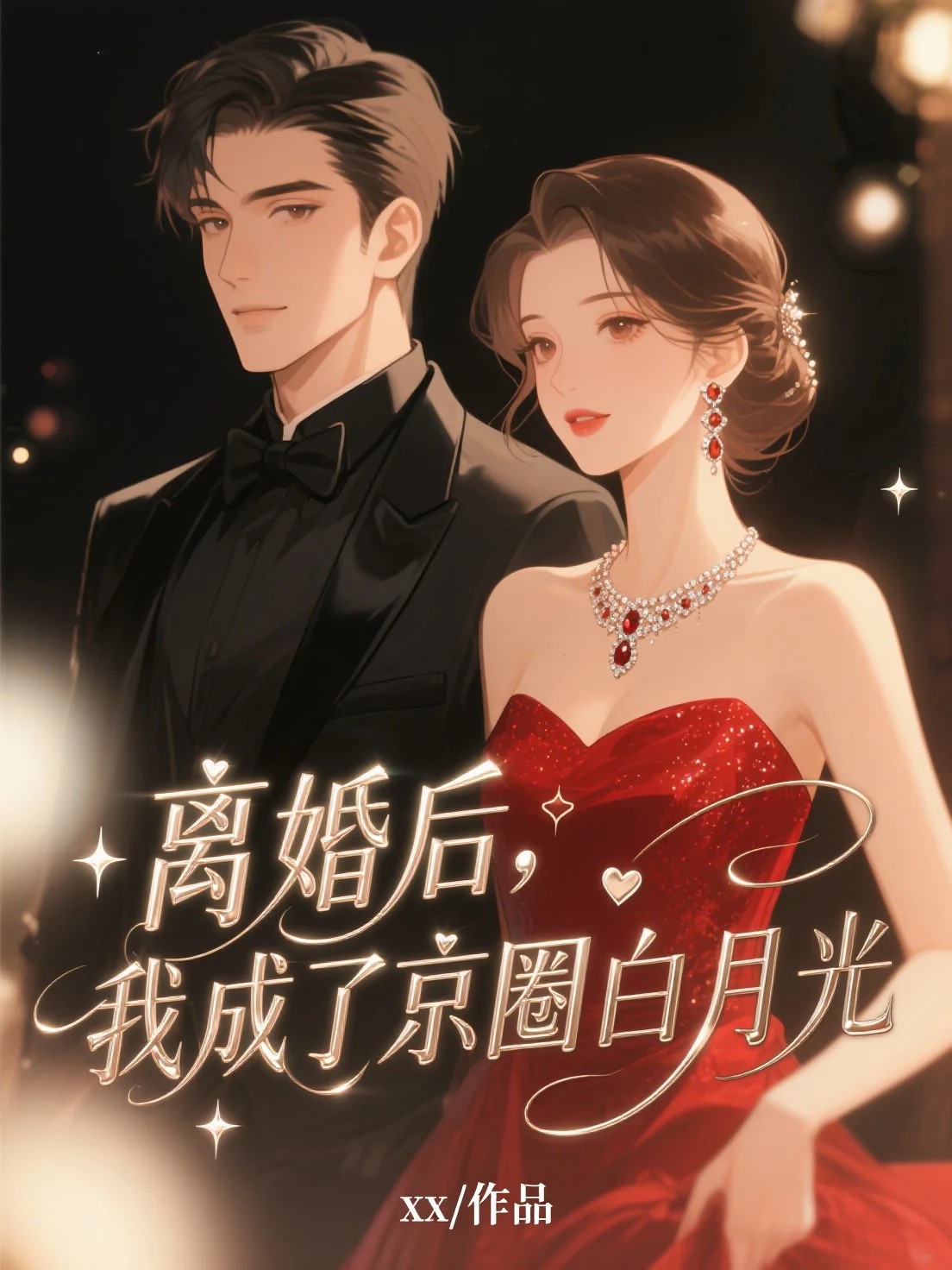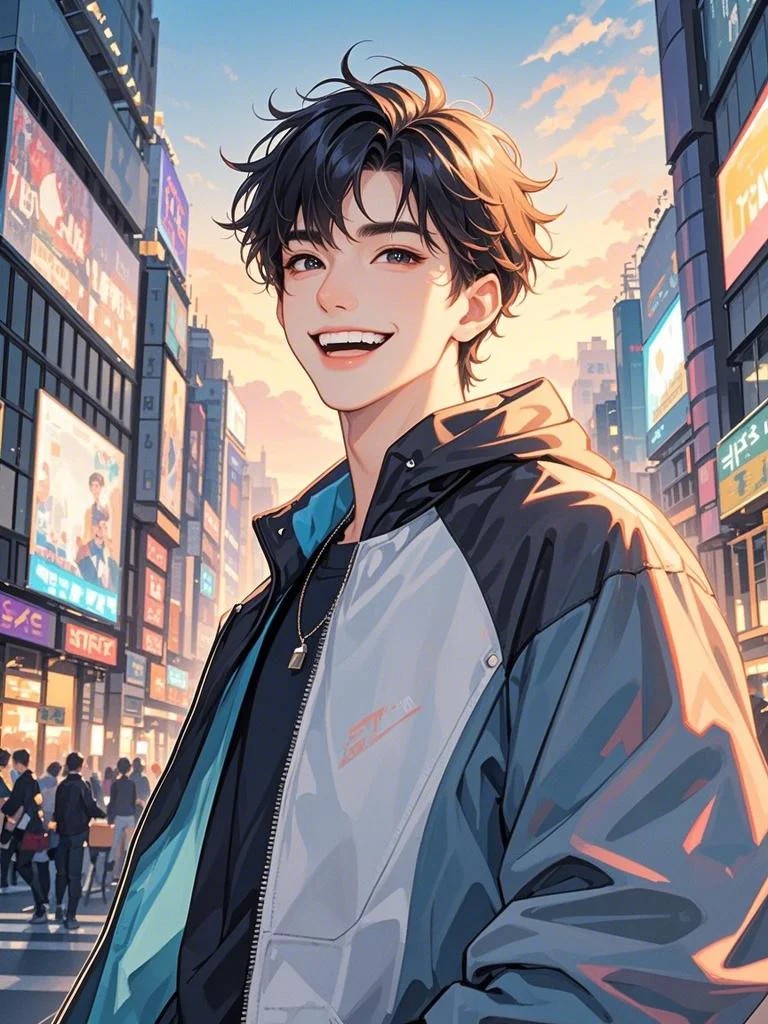那位海归张先生也很快到了。戴着金丝眼镜,穿着休闲西装,气质斯文,谈吐间确实带着几分学院派的清高。看到林晚时,他眼中闪过一丝惊艳和意外。
“这位是?”张先生看向苏蔓。
“这是我最好的闺蜜,林晚!建筑保护师,对艺术可有研究了!”苏蔓立刻把林晚推上前线。
林晚无奈,只得礼貌微笑:“张先生你好,叫我林晚就好。陪蔓蔓来看看,谈不上研究。”
三人走进美术馆。展览主题颇为晦涩,抽象的线条、扭曲的形体、强烈的色彩碰撞,确实不是一般人能轻易理解的。张先生兴致勃勃,对着几幅作品侃侃而谈,引经据典。苏蔓听得云里雾里,只能在一旁尴尬地赔笑,不时向林晚投来求救的眼神。
林晚虽然主攻古建,但对艺术史和现代流派也有涉猎。她看着眼前一幅用废旧金属和木材拼贴的巨大作品,那扭曲挣扎的形态和斑驳的质感,让她莫名联想到工作室里那些伤痕累累却依旧坚韧的金丝楠木。她忍不住轻声开口:
“这幅作品……虽然形式先锋,但内核充满了挣扎与再生的力量。艺术家用废弃的材料,通过解构和重组,赋予它们新的生命和表达,恰恰暗合了‘不破不立’的东方哲学。这种对‘旧物’的尊重和转化,其实和古建修复中‘修旧如旧’的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
她的声音不大,语调平和,却清晰地点出了作品表象下的深层意涵,既没有附和张先生那些晦涩的理论,又巧妙地联系了自己的专业,给出了一个独特而令人信服的视角。
张先生惊讶地看向林晚,眼中充满了欣赏:“林小姐见解独到!将先锋艺术与东方修复哲学联系起来,这个角度太新颖了!您对‘材料’和‘再生’的理解,确实深刻!”
苏蔓也松了一口气,对林晚投来崇拜的目光。
接下来的看展过程,张先生的话题有意无意地更多转向了林晚。林晚虽然只是礼貌回应,但她的专业素养和沉静气质,显然给这位海归精英留下了极好的印象。苏蔓反倒成了陪衬,不过她乐得清闲,只要不让她谈艺术就行。
林晚没有注意到,在美术馆二楼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一个戴着鸭舌帽和口罩的身影,正举着手机,镜头无声地对准了他们三人,尤其是林晚与张先生交谈时的侧影。
看展结束,张先生意犹未尽,提议去美术馆顶楼的咖啡厅坐坐。苏蔓想拉林晚一起,林晚却婉拒了:“不了,我工作室还有点事要处理。你们聊。” 她不想当电灯泡,更不想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告别了苏蔓和张先生,林晚独自走出美术馆。夜晚的城市华灯初上,凉风习习。她深吸一口气,感觉紧绷的神经舒缓了一些。刚走到路边准备打车,一辆黑色的宾利慕尚无声地滑到她面前停下。
后车窗降下,露出沈聿白那张轮廓分明的侧脸。他穿着深色衬衫,没系领带,领口随意解开一颗纽扣,在夜色中更显冷峻。他转过头,深邃的目光落在林晚身上,带着惯有的审视和一丝……难以捉摸的意味。
“上车。”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
林晚微微一怔。他怎么会在这里?巧合?还是……她下意识地环顾四周。

修复时光与你林晚沈聿白番外+无删减版
推荐指数:10分
很多朋友很喜欢《修复时光与你林晚沈聿白番外+无删减版》这部古代言情风格作品,它其实是“vv33”所创作的,内容真实不注水,情感真挚不虚伪,增加了很多精彩的成分,《修复时光与你林晚沈聿白番外+无删减版》内容概括:她用双手修复文物,他用契约买断人心。一场价值三百万的交易,能否修复两颗破碎的灵魂?林晚,才华横溢却濒临绝境的古建修复师,守护着摇摇欲坠的工作室与心中的文化净土。沈聿白,冷酷强势的科技新贵,坐拥庞大商业帝国,却深陷家族联姻的冰冷桎梏。一场各取所需的冰冷契约,将他们捆绑在一起:他需要一位“完美妻子”抵挡催婚风暴,稳固商业版图。她需要三百万救命资金,守住毕生守护的古老技艺与精神家园。...
第45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