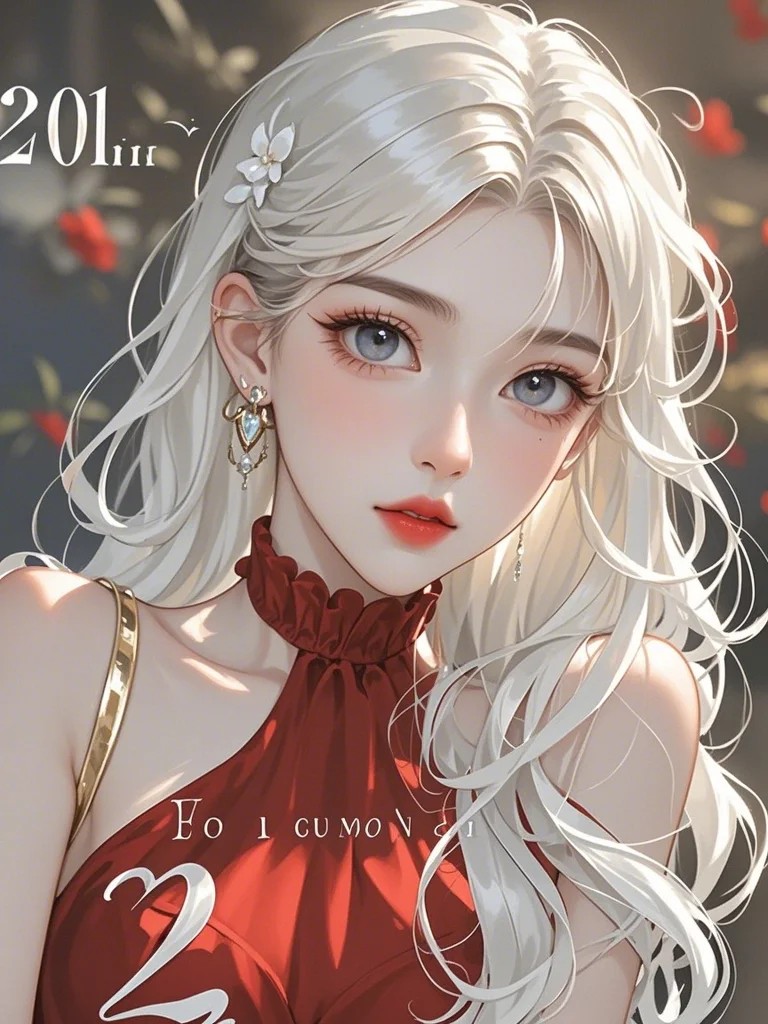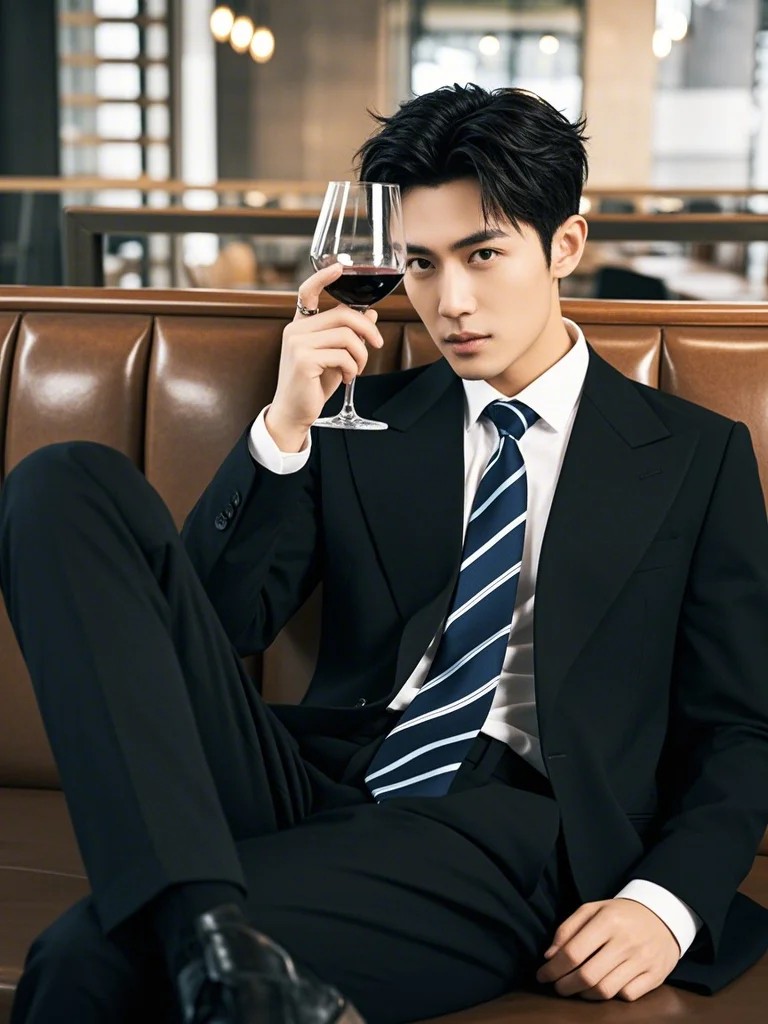沈惊寒接过诗稿,目光落在她皓腕上的玉镯——是前日吏部侍郎家公子送来的贺礼,苏婉清转手就戴在了手上。他忽然想起林砚那张被油烟熏得发黄的账本,上面的字迹歪歪扭扭,却比这诗稿更实在。
变故发生在考前七日。沈惊寒发现自己常用的那方砚台被动了手脚——砚底被人钻了个小孔,灌了些墨汁般的液体,闻着有淡淡的杏仁味。他不动声色地把砚台收进匣子,转身对伺候笔墨的小厮说:“这几日辛苦你了,去账房领双倍月钱吧。”小厮脸唰地白了,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原来是原身得罪过的远房表兄指使的,想让他在考场上写出的字晕成一团,失了功名。沈惊寒没声张,只叫人把小厮送回了家。夜里,他对着那方砚台坐了许久,月光从窗棂漏进来,在砚台上淌成一条银线。他忽然明白,这科举之路,从来都不只是笔尖上的较量。
他开始做更周全的准备:把常用的笔墨纸砚都换成新的,贴身带着;每日的茶水饭菜,都让忠心的老仆先尝一口;甚至连去考场的路线,都让小厮提前踩了三遍点,记下哪里有岔路,哪里可能藏人。
考前最后一日,沈惊寒把自己关在书房,对着空白的纸卷,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他忽然很想知道,林砚此刻在做什么。是在清点外卖队的账本,还是在给新会员发卡?那个江南小镇的青年,凭着一股蛮劲在陌生的时代扎根,倒比自己这个尚书公子更洒脱些。
窗外传来喜鹊的叫声,苏婉清捧着个红布包进来,脸上是恰到好处的关切:“表哥,明日就要进考场了,这是我求来的平安符,你带着。”红布包里除了符,还有几颗蜜枣,寓意“早中”。沈惊寒接过时,指尖不小心碰到她的手,她像受惊的小鹿般缩回,耳尖却红了。
送苏婉清出门时,沈惊寒瞥见她袖口露出的半张纸条,上面似乎写着“林砚”二字。风卷着槐树叶落下来,盖住了那字迹,也吹起了他衣袍的一角——里面藏着他熬夜画的考场地形图,每个拐角都标着记号。
夜深了,沈惊寒把整理好的考具——笔墨、干粮、薄毯,一一装进考篮。最后放进去的,是那方被动过手脚的砚台。他要带着它进考场,不是为了记恨,而是要提醒自己:往后的路,只会比这更难走。
远处更夫敲了三记梆子,沈惊寒吹灭烛火,月光涌进房间,照亮他年轻却坚毅的脸。院试的考场就在前方,而他不知道的是,千里之外的江南,林砚正对着一张州府地图发愁——那张警告他“莫要趟过界”的字条,笔迹竟与今日苏婉清掉落的那张纸条,有几分相似。
明天,他要走进考场,而林砚,大概正盘算着如何走出江南。两条看似平行的线,已在无人知晓的地方,悄悄缠绕在了一起。
上
江南的梅雨刚过,空气里还飘着湿漉漉的青草气,林砚的外卖队已经像雨后的春笋般,冒出了新的气象。
王二柱踩着新买的青布鞋,正给会员名册上的名字画红圈,笔尖在“张秀才”三个字上顿了顿,忍不住咂舌:“老板,您看这张秀才,自打中了童生,几乎天天用会员券点酒楼的菜,说是要‘犒劳苦读的自己’,这哪像是苦读的样子?”

双穿一个搞钱一个掌权,顺便恋爱林砚沈惊寒无删减+无广告
推荐指数:10分
军事历史《双穿一个搞钱一个掌权,顺便恋爱林砚沈惊寒无删减+无广告》目前已经迎来尾声,本文是作者“Aurora之恋”的精选作品之一,主人公林砚沈惊寒的人设十分讨喜,主要内容讲述的是:当现代外卖总监林砚与金融系天才沈惊寒同时穿越至大明朝,一个沦为好吃懒做的市井流民,一个成为臭名昭著的纨绔贵胄。两人在科举与商道的双线逆袭中,从互不相识的陌生人逐渐成为生死与共的盟友。林砚以\...
第21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