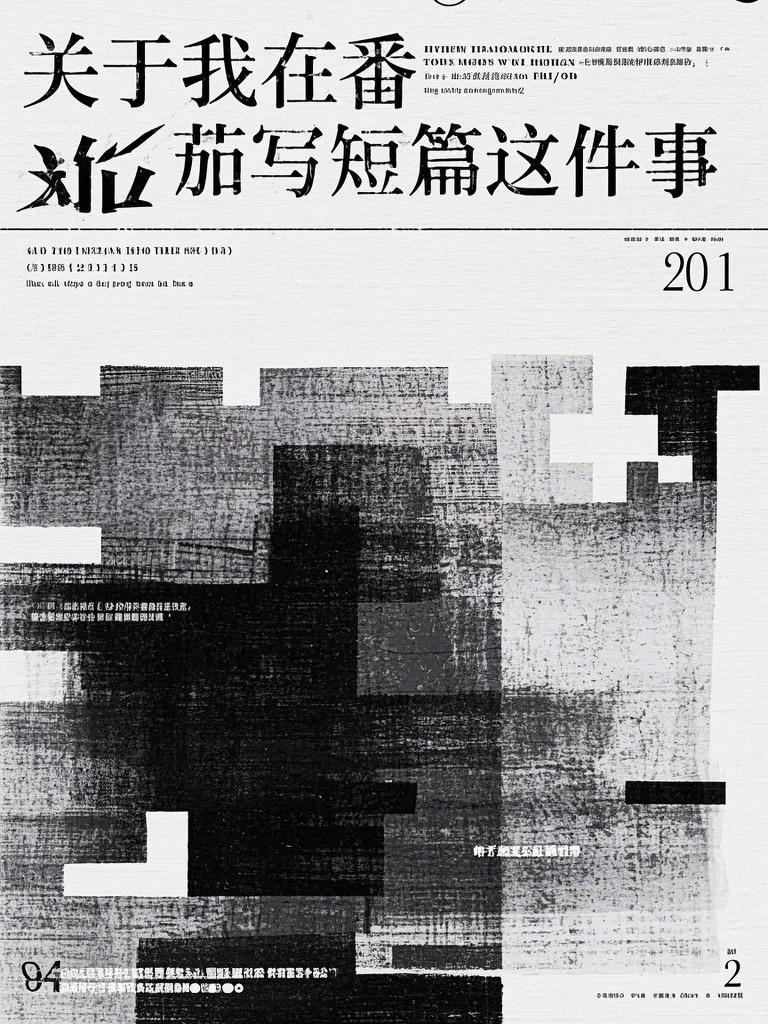主持人还在锲而不舍地挖掘着《昭》背后的故事,问题更加直白露骨。
江临依旧是那副温文尔雅、滴水不漏的姿态,谈着音乐理念,谈着创作历程,偶尔瞥向镜头的眼神深邃平静,仿佛刚才休息室里那短暂的交锋从未发生。
可我却再也无法平静。
那些信纸上的字迹,那些“未来的妻子”,那个被反复描摹的“沈昭”……像无数根烧红的针,密密麻麻地扎在我的神经上。
他修长的手指在琴弦上无意识地抚过,我仿佛看到了他深夜伏案,在那些泛黄信纸上落笔时的专注侧影;他微微弯起唇角回答问题时,我脑中浮现的却是他写下“笨蛋沈昭”时,那强压着宠溺和无奈的叹息;他说着“沉淀的声音”,我耳边轰鸣的却是他笔尖流淌出的那句“当哥哥,就能一辈子赖着她了”……导播间里其他人的交谈、机器的噪音都变成了模糊的背景音。
我的世界只剩下监视器里那个男人,和他那些被时光尘封、却在此刻被我窥见天光的、沉重到令人窒息的心事。
原来每一次的挺身而出,每一次的默默守护,每一次轻描淡写的“举手之劳”,甚至每一次用“妹妹”划下的冰冷界限,都是他在绝望的独木桥上,用尽力气维持着靠近我的姿势。
一股巨大的、混杂着心疼、愧疚和某种破釜沉舟的冲动,像沸腾的岩浆,在我胸腔里横冲直撞,几乎要冲破喉咙。
不能再这样了。
不能让他再对着一个“未来的妻子”倾诉,而那个“妻子”却像个瞎子一样,把他所有的深情都当成了理所当然的“兄妹情”!
我要一个答案!
现在!
立刻!
导播的声音再次响起,带着一丝疲惫的解脱:“好!
"

所有公开的乐章都是私奔的邀请函最新章节
推荐指数:10分
长篇现代言情《所有公开的乐章都是私奔的邀请函》,男女主角缪斯江临身边发生的故事精彩纷呈,非常值得一读,作者“喜欢文须雀的吕主任”所著,主要讲述的是:我和江临青梅竹马二十年,全世界都知道他喜欢我。除了我。他为我打架断过腿,熬夜补过课,连我分手都是他收拾的烂摊子。可他说:“你永远是我妹妹。”直到我在他书房发现一叠泛黄的信纸,每张开头都写着“致未来的妻子”。而最新那页,是我的名字。录音棚里他正为新专辑调音,我闯进去按下静音键。“江临,你谱子里那些音符......
第13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