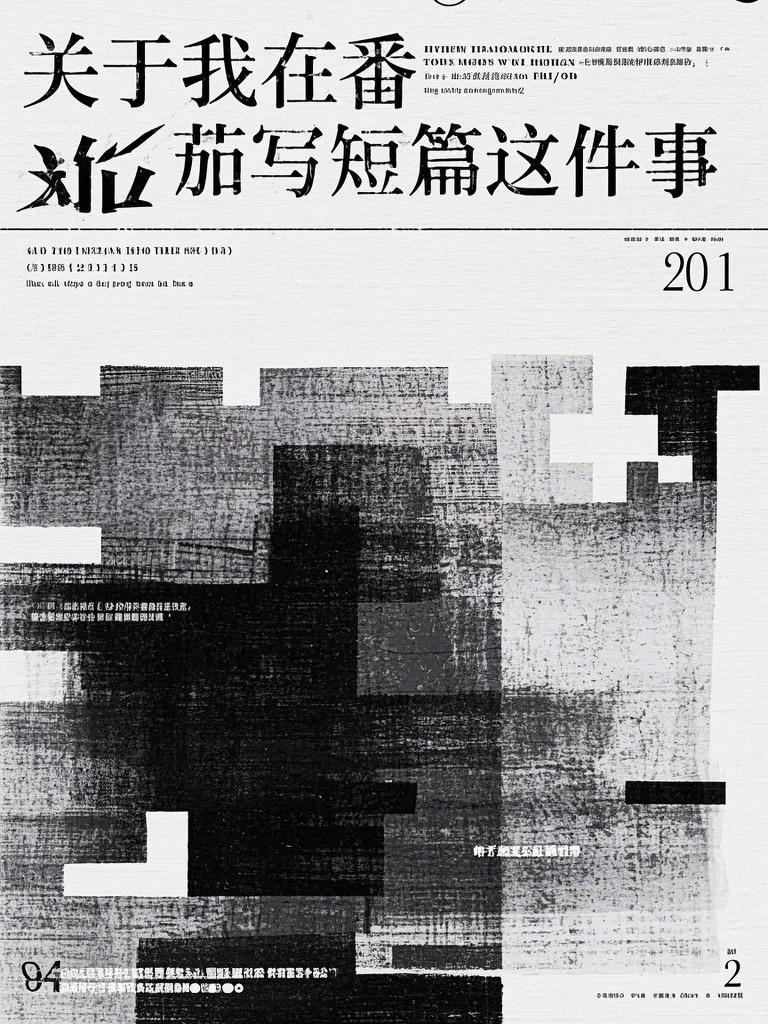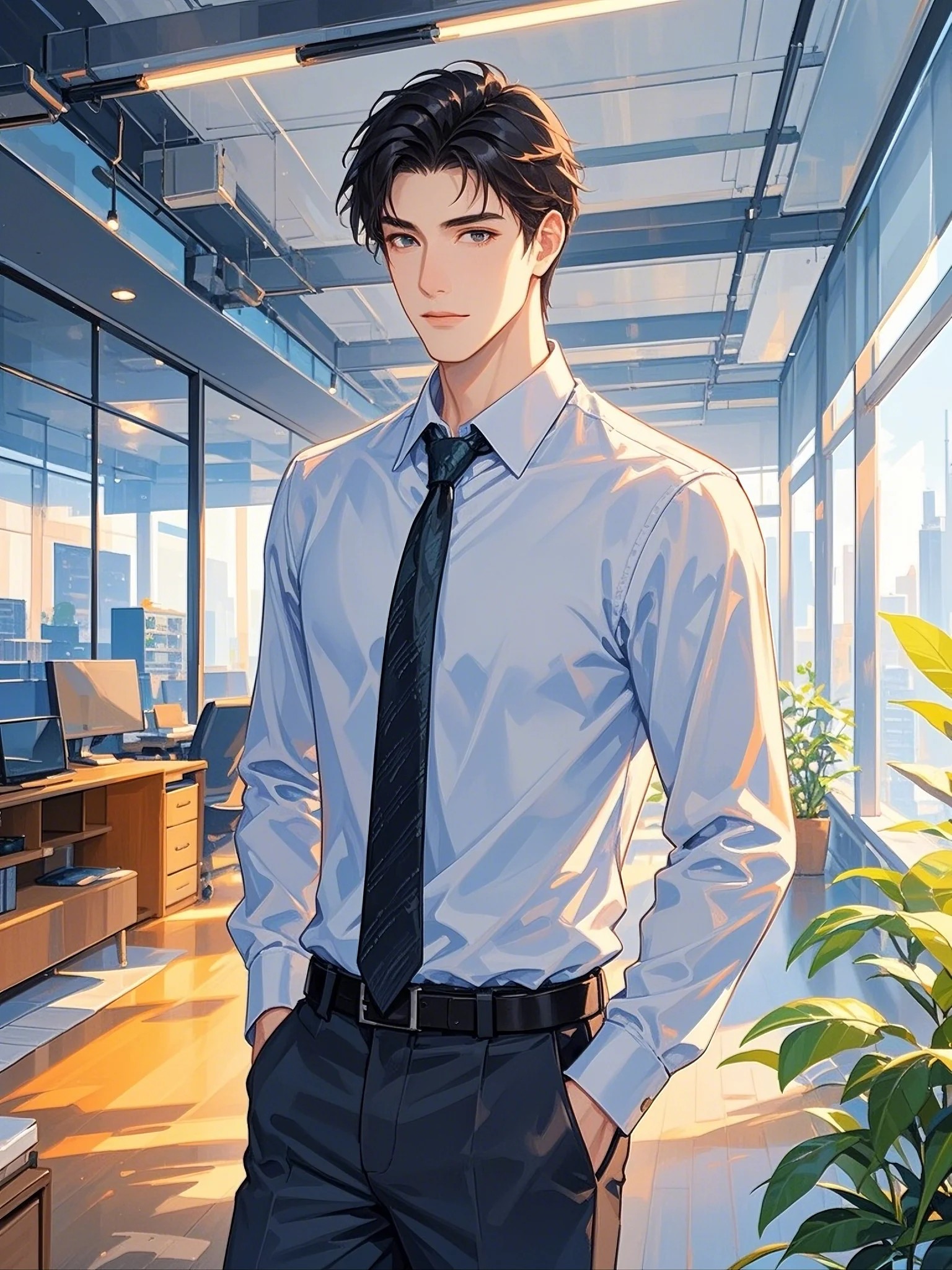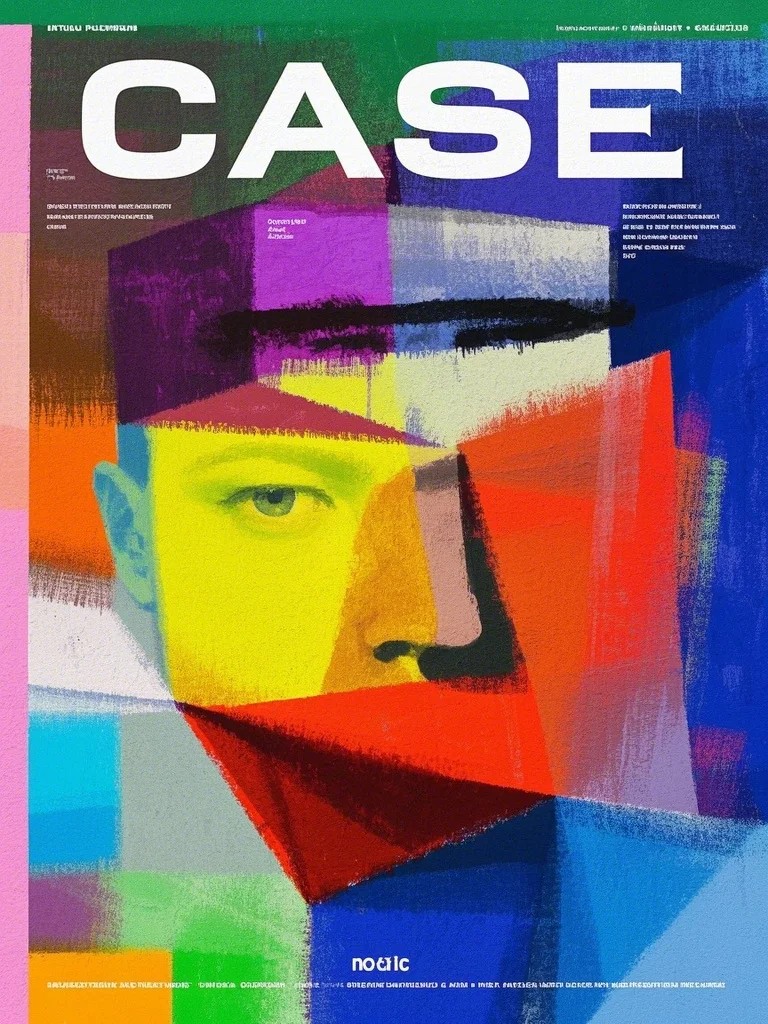崇祯忆起,现任户部乃是李待问。这人清正廉洁、刚正不阿,只可惜生逢明末,财政已然崩溃,纵有满腔抱负,却也无力回天。
崇祯十五年,李待问因病辞官,前往天津养老。后来听闻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荡了秋千,李待问在天津挥笔写下绝命诗 “血泪已枯心更赤,遗骸犹望护山河”,随后服毒自尽,以死殉国。
崇祯眉头渐渐锁紧。他忽然意识到一个令人窒息的悖论——这个王朝明明还有那么多忠贞之士,为何最终却像沙塔般轰然崩塌?
"大伴!"他的声音有些沙哑,"你说...我大明朝也不全是贪官污吏,也有这么多的爱国忠君之人,为何大明会变成现在这个模样?"
王承恩手中的拂尘微微一颤:"皇爷,老奴愚钝..."
崇祯却已陷入沉思。他看向面前的奏章,前日兵部呈上的塘报里,那个带着三百残兵死守雁门关的参将;想起三司会审时,那个宁受廷杖也不肯诬陷同僚的给事中;更想起昨夜通政司送来的密奏中,那个变卖家产募兵的致仕侍郎。
这些人分明都怀着赤胆忠心,可为何...
"就像一具遍体鳞伤的躯干,"崇祯突然喃喃自语,"纵有几分完好的血肉,也抵不过溃烂的创口。"他猛地攥紧案上的塘报,纸张在掌中发出痛苦的呻吟。
王承恩吓得跪倒在地:"皇爷保重龙体..."
"朕没事。"崇祯松开手,他忽然明白了——李待问们的悲剧,不在于他们不够忠勇,而在于他们每个人都像在填补一个无底的漏卮。
当整个官僚体系已经腐朽到根子里,再多的忠臣良将,也不过是往将倾的大厦上添几根无用的椽子。
窗外传来梆子声,已是吃午饭的时间了。崇祯望着烛台上堆积的奏折,忽然想起李待问绝命诗里那句"血泪已枯心更赤"。或许,这就是答案——当忠诚化作绝望的泪水流尽时,剩下的那颗赤心,终究敌不过历史的洪流。
满脸疲惫地坐在龙椅上,眼神中透着焦虑与急迫。听闻脚步声,他抬眼望去,只见户部官员李待问匆匆步入殿内,身形略显佝偻,神色亦是憔悴不堪。
李待问刚踏入殿门,便 “扑通” 一声跪地,高声道:“陛下,微臣李待问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崇祯急切地摆了摆手,说道:“李卿,免礼平身,先坐,等骆养性来了一起说。
李待问满心狐疑,心中诧异之情如潮水翻涌。
忆起前些时日,为了给松锦前线筹措至关重要的军饷,他在文华殿外长跪不起,整整熬过两个时辰,膝下石板冰冷刺骨,可那紧闭的殿门却始终未开,皇帝更是对他的苦求置若罔闻。
往昔的被漠视与此刻突然被召见形成鲜明反差,他实在想不明白,这位行事愈发让人捉摸不透的皇帝,此番唤他前来,又把那令人敬畏的特务头子一并招来,究竟所为何事?
思绪万千间,他根本无暇细想,脚步有些僵硬地随着指引在一旁落座,大气都不敢出,只是低垂着头,偷偷用余光打量着殿内情形,双手不自觉地在袖笼中微微颤抖 。
崇祯此时也并未搭话只是提笔在宣纸上疾书数行:
一征调寺庙:着大隆善寺、护国寺等僧众一月内纳粮十万石
二搜刮勋贵:以把控京营,吃空饷为罪名,对成国公、定国公府抄其家产钱粮以充国库
三命锦衣卫前往朝鲜安南借粮,并前往福建收罗番薯,土豆并在北方大力推广
写罢,将宣纸递给了一旁的李待问说道:“李爱卿,看看吧,钱粮的事朕已经给你解决了。”
李待问双手接过指令,只匆匆一瞥,顿觉一股寒意自脊背蹿升,当即 “扑通” 一声,双膝跪地,声音颤抖,带着几分急切与惶恐,高声谏言:“陛下,此计万不可行呐!
成国公、定国公府在勋贵阶层中威望颇高,树大根深。若贸然对其抄家,无异于在勋贵群体中扔下一颗巨石,激起千层浪。
届时,整个勋贵阶层必然人人自危,如惊弓之鸟。他们平日里盘根错节,人脉广布,一旦心生恐惧与不满,极有可能抱团联合,公然对抗朝廷。
如此一来,朝堂之上,政令恐难畅通;朝野之间,动荡必将滋生,国家根基亦会随之动摇,陷入风雨飘摇之险境。恳请陛下三思而后行啊!”
崇祯闻言,目光微沉,并未立即回应李待问的谏言。殿内一时静默,只听得铜漏滴答作响。
王承恩见状,趋前一步低声道:"皇爷,骆指挥使与李千户已在殿外候旨。""

明史看到一半,我穿成了崇祯帝!结局+番外
推荐指数:10分
由小编给各位带来小说《明史看到一半,我穿成了崇祯帝!》,不少小伙伴都非常喜欢这部小说,下面就给各位介绍一下。简介:我是历史系研究生,周末在图书馆看明史时,被炸雷劈到穿越成崇祯帝。睁眼就在紫禁城东暖阁,老太监哭着喊皇爷,太医说我受惊吓气血不畅。得知此刻是崇祯14年松山大战时,大明危如累卵。我深知责任重大,强压震撼,模仿帝王口吻安抚众人,从此刻,我要以崇祯身份,力挽狂澜救大明。...
第10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