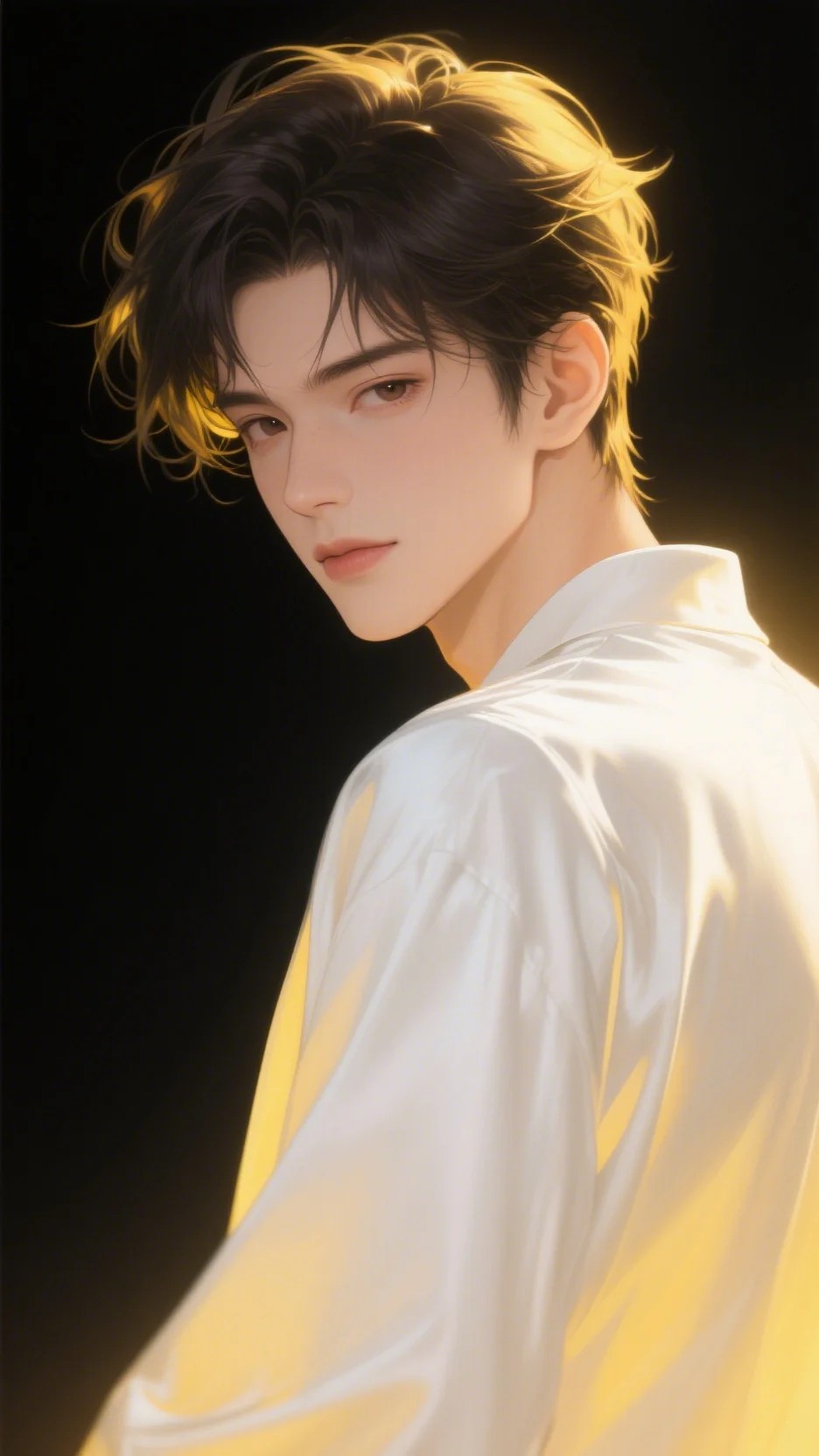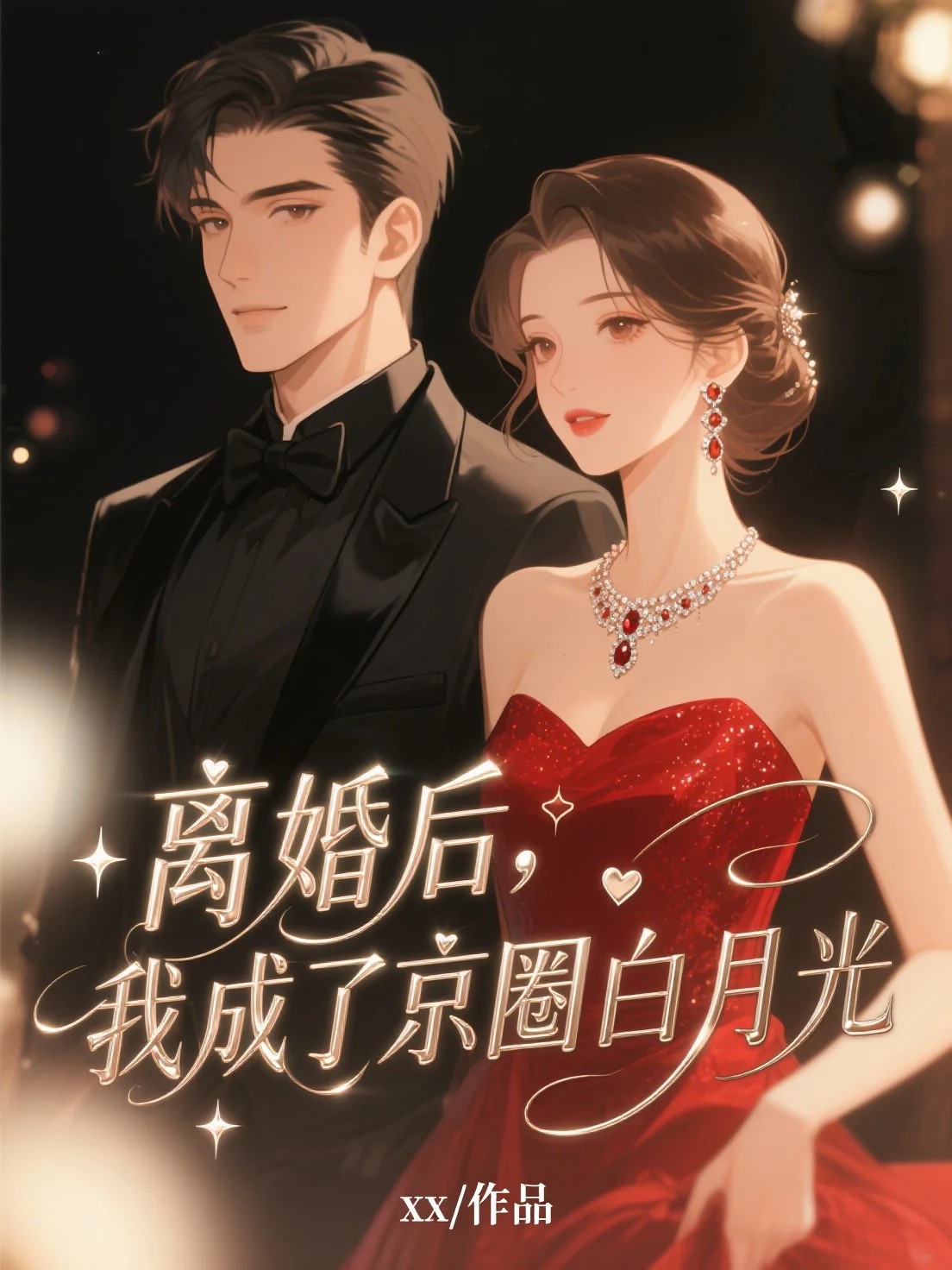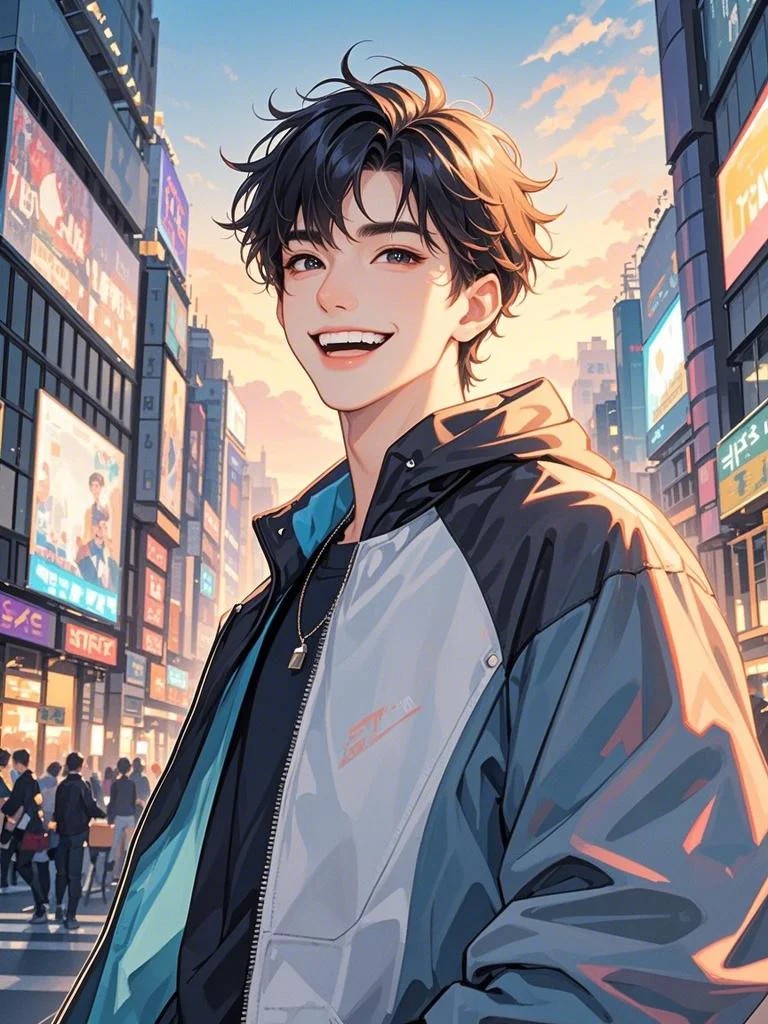昔年宋朝仁宗即位之初,太后临朝,刘氏之家四方皆入要职,士人噤言,朝廷空壳。司马光言:“外戚之家,非国家之福。”臣不敢妄比今事,然朝局之势,臣心惴惴,日夜难安。
臣顾氏一门,自先祖起以直言受罚,至臣犹不敢忘先训。臣闻宫中有议:待殿下即位,当托以太后之策,纳贤姬数人、广纳外族之恩,渐归权柄。臣愚见以为,此皆权谋之网,虽甘如饴,实乃毒药耳。
桷高台建,若非己凿之基,则终为人倾。高皇祖曾戒宗亲曰:“莫使家国一体,莫使权出宫闱。”今朝之局,未可轻许信任。
臣不才,亦未敢逆潮势而强谏,惟以此信藏于书末,望殿下有朝一日权柄在握,能记此言。若届时尚觉臣言可取,亦可念顾氏不为权趋附,乃为社稷、为殿下长安而语也。
臣年事已高,恐不得见大成之日。惟愿殿下登高自持,不负清名。”
言辞之间,竟是暗示萧彻当年太后的郁家之力不可借,否则日后外戚干政,如藤蔓绞杀松树,早晚将让自己落入死路之中。
而后,竟还有萧彻的回信,信件的内容极为简略,字句之中却带着一股隐忍和决绝。
“老师忠言,铭感于心。
然局中人已无回舟之岸。
前路虽覆火,但生死只在此行。
老师若执意相阻,休怪烈流断堤,无情吞人。”
这两封信夹杂在策论之中,誊抄的字迹也与其他不同,誊抄者笔锋锋利肆意,带着一股不凡的气度。
而其间的深意,也令沈晚意愈发困惑起来。
从这信中看,萧彻对沈鼎泰谈得上敬重,萧彻还常称他为“老师”。
可似乎就是宸妃死后,萧彻被当时还是宁贵妃的太后抚养,便立刻换了太傅,此后二人再无言辞交往的记录。
而这两封信的时间,正是萧彻登基的前一年秋天。
那时候先帝已经病入膏肓,太子和二皇子之间的党争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就在这最紧张最需要小心的时刻,沈鼎泰竟然给萧彻写了这样一封信。
而萧彻言辞之间,竟称自己为“局中人”。
沈晚意自然知道,萧彻能够上位,除却他自身的手段,最重要的是他背后的太后母家郁家给予的支持。
萧彻登基之后,郁家家主立刻掌握了兵权,一时间将外戚的权利放大到了最大。
而这也是萧彻执政三载,最令人诟病之处。
自古以来,外戚干政都是各代帝王最忌惮的事情之一。
而萧彻十六岁登基,所娶的皇后亦是郁家女子。当时朝野上下不少人诟病现如今的皇帝不过傀儡。
可这三年,萧彻已经一点点地把朝中局势翻了半边天,他引清流入朝,改制宗族制度与田亩制度分权,又将张岑一党无声无息地扶持起来,如今朝中几乎是三家分立的局势。
以郁家为首的贵族与外戚,以张岑为首的文臣和其学生,还有近两年在科举中被萧彻另开一条通道直接选拔上来的清流寒门子弟。
连霍家,原本也已经落寞多年,也是萧彻近两年提拔上来的武将世家之一。
沈晚意盯着那封信发呆,她隐约地觉得一切都没有那么简单,可又始终难以将这书信中被祖父恳切相劝的形象和如今那个恶劣又无法无天的帝王合在一起。
他看起来可不是祖父会欣赏的人选。"

君夺臣妻,被年下疯批帝王盯上了无删减版
推荐指数:10分
无删减版本的现代言情《君夺臣妻,被年下疯批帝王盯上了》,成功收获了一大批的读者们关注,故事的原创作者叫做与风酌,非常的具有实力,主角萧彻沈晚意。简要概述:【疯批年下帝王*清冷禁欲权臣美人】【姐狗文学】【前期强制爱】【多男配雄竞】【非双洁】新婚夜,她以为夫婿薄情,要她一夜便离她而去,三年未归。三年后才知,那夜误入她闺房、强取豪夺的,是那位少年登基、手染鲜血的疯批皇帝。她成了天子心头的隐秘执念,囚于金笼,寸步难逃。抵死缠绵中,年轻的帝王声音发颤问她:“你心里…到底有没有半分朕的位置?”...
第47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