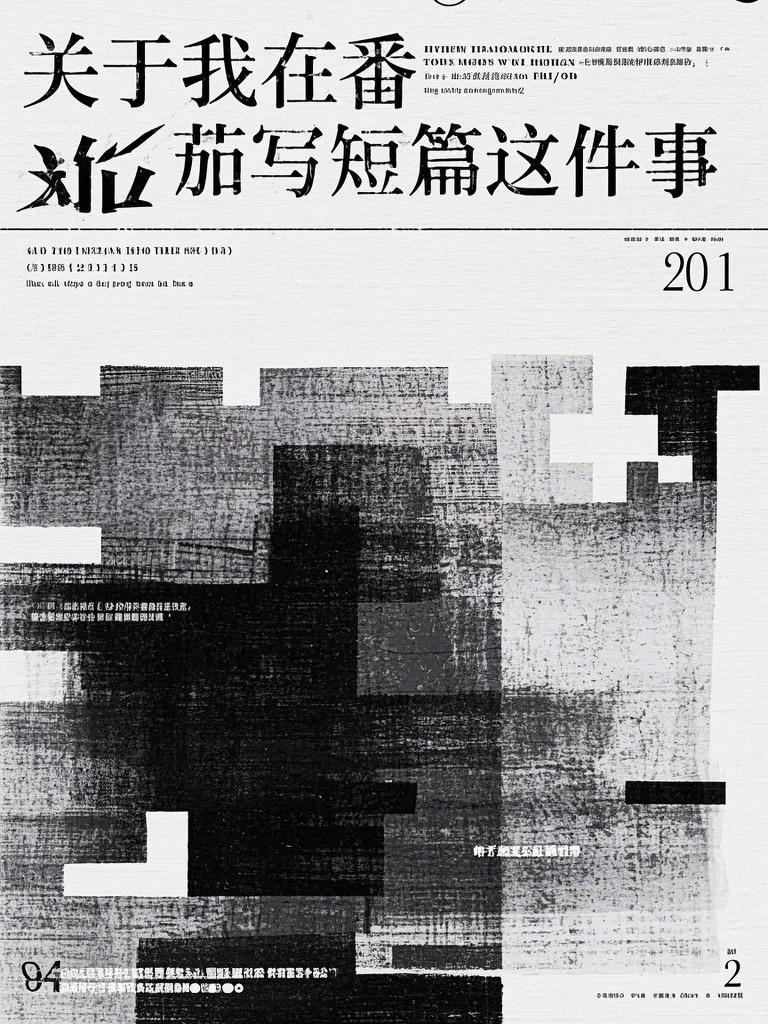“还要脱裤子吗?”姜媃有些尴尬。
与他分开五年。
她实在不太好意思这么暴露在他面前。
权宴自顾自戴上乳胶手套,拿出检查用的小手电筒,啪嗒,刺目的电筒光亮起来,他站在检查床边说:“不检查,我怎么知道你是感染哪种红疹?”
这话,没毛病。
姜媃也不是医生,不好反驳他的专业。
甚至不敢挑刺。
只是秉持愧疚,她终究无法直视他那双曾经迷倒众生的深黑色的眸。
这双眼眸,在与她鬼混厮磨的一个月内,看尽她被他用这双做手术的手,抚摸过后情动的风花雪月和所有嫣红失态。
那时候,她撩他,勾引他。
把他从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岭之花拉下神坛。
委身在她石榴裙下。
她想,那一个月的厮磨是有成果的。
哪怕他不曾说一句也是喜欢她,但他真情实感咬着她耳尖说:要不要跟我交往试试?
看起来,她真的把他诱摘下来了。
只是——后来厮混太浓,他没有等到她答应交往,她提前跟他结束了。
那时候,姜家还没倾覆。
而她约他见面要让他滚,不和他玩了。
那天晚上的谈判,她高高在上,眼底都是刻意的讽刺和嘲弄,十足十扮演了一个玩弄男人的‘坏女孩’。
然后她看到他眼底有恨意,唇角嗪着阴冷到骨子的轻笑:“原来是跟我玩玩?嗯,好,到此为止。”
姜媃想,他恨死她了。
姜媃这几年,每年都会做噩梦。
梦里都是权宴掐着她脖子,眼眸泛红,要把她掐死泄愤的样子。
他会咬着牙,淬毒般地说:“你敢玩我?”
“姜媃,你怎么敢的?”
她也想过,回来道歉。
可是一想到自己的状况和处境,她只能什么不做。
坏女孩,做了坏事。
只能一路坏到底。"

权医生,甩你的白月光带崽回国了热门小说
推荐指数:10分
火爆新书《权医生,甩你的白月光带崽回国了》逻辑发展顺畅,作者是“苏苏兔”,主角性格讨喜,情节引人入胜,非常推荐。主要讲的是:【玩高岭之花玩一半跑路消失,追妻酸甜,破镜重圆,女甩男,悲惨男主被玩出心理疾病,五岁女宝,久别重逢,明艳落魄女导演V清冷太子爷医生兼娱圈资本大佬,男主先医后从商】*太子爷嘴硬超爱*京圈太子爷医生权宴,俊美禁欲又克己复礼,这样的人,所有人都觉得他很难动情。5年前,还没破产的大小姐姜媃看上他,下了猛套路引诱京北校草下神坛,两人在酒店厮混足足一个月。一个月后,太子爷身心沉沦结果姜媃甩了他,不久姜家和姜媃从帝都消失。五年后姜媃回国当导演,再遇,她腿部皮肤过敏,不巧挂了他的号。姜媃内疚主动打招呼:“权宴,好久不见。”被甩的男人脸色冷淡:“我和你不熟。”姜媃识趣,不再打扰他,某日拉投资又碰上他,在场所有人都等着她被权宴报复,封杀。结果男人却在昏暗角落圈她入怀:“姜媃,跟我结婚。”“你欠我,我也可以帮你。”姜媃想拒绝,但后来只能折腰。婚后,她以为男人会报复她?谁知男人每天抵死缠绵,夜夜不停,发狠要造三胎,姜媃吃不消想跑,男人气的将她抵在怀里,竟然哭了,手指掐的紧紧:“媃媃,又想把我甩了?我等了你五年,别再欺负我。”再后来,他脱下白大褂亲手为姜家洗清冤屈,扶她上青云。...
第6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