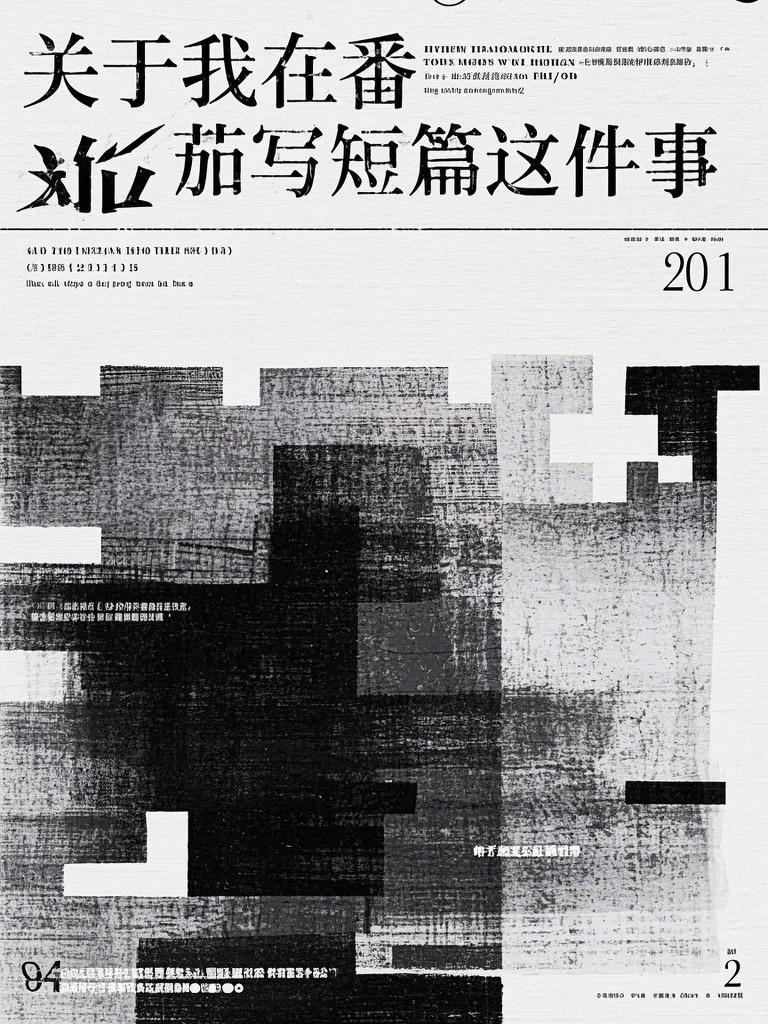箱子“哐当”一声墩在堂屋地上,震得八仙桌上的搪瓷缸子嗡嗡响。
那扇老木门“吱呀——”拖得老长,声音像钝刀子割木头,还是跟记忆里一模一样。
堂屋里光线有点暗,灰尘在斜射进来的光柱里跳舞。
妈正踮着脚,身子绷得直直的,胳膊伸得老高,手里一块半湿不干的抹布,正跟冰箱顶上那层陈年老灰较劲呢。
日头穿过糊着旧报纸的窗户格子,把她弯得像张弓的后背照得发亮,几缕花白的头发从发髻里溜出来,黏在汗津津的脖子上。
“妈。”
我嗓子有点干,喊了一声,声音在空荡的堂屋里显得有点突兀。
她猛地一扭头,脸上“唰”一下,像被点亮的灯泡,瞬间笑开了花。
眼角的皱纹密密麻麻挤成一团,活像被揉烂又展开的作业纸。
“哎哟喂!
可算回来了!
我的祖-宗!”
她声音拔高了八度,透着股久别重逢的喜气,“你-爸!
天没亮就窜菜市场去了,跟打了鸡血似的!
"

上海三十万年薪,败给妈的广场舞精品推荐
推荐指数:10分
今天安利的一篇小说叫做《上海三十万年薪,败给妈的广场舞》,是以抖音热门为主要角色的,原创作者“灵犀梦语”,精彩无弹窗版本简述:箱子“哐当”一声墩在堂屋地上,震得八仙桌上的搪瓷缸子嗡嗡响。那扇老木门“吱呀——”拖得老长,声音像钝刀子割木头,还是跟记忆里一模一样。堂屋里光线有点暗,灰尘在斜射进来的光柱里跳舞。妈正踮着脚,身子绷得直直的,胳膊伸得老高,手里一块半湿不干的抹布,正跟冰箱顶上那层陈年老灰较劲呢。日头穿过糊着旧报纸的窗......
第1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