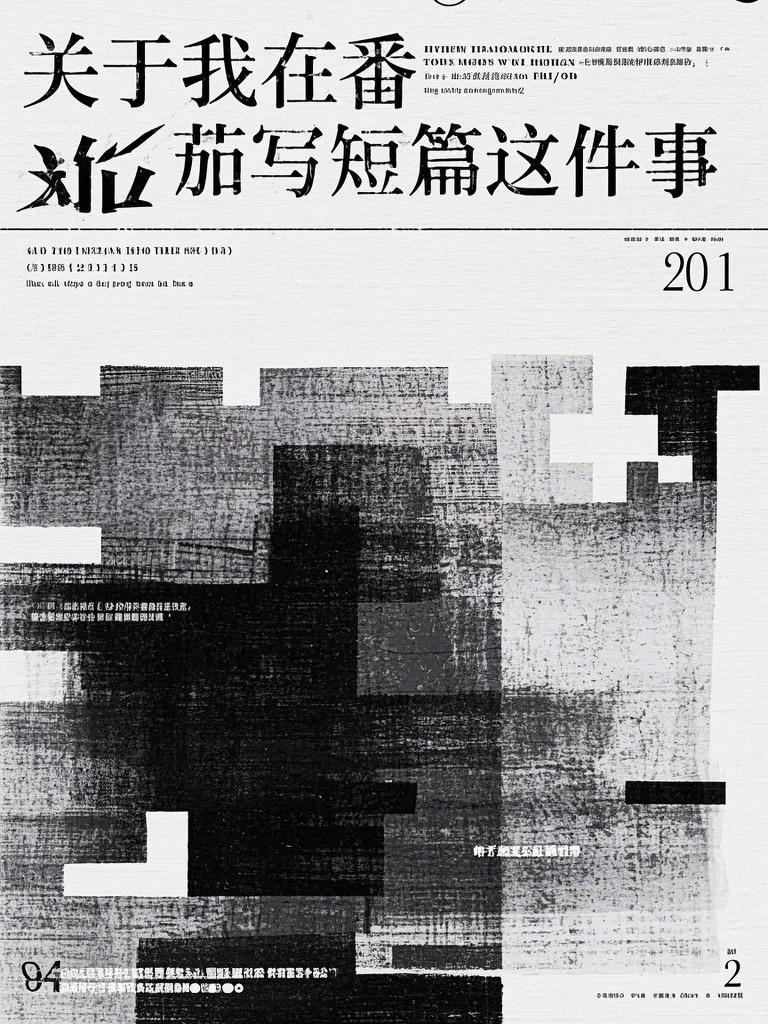这句话落下,像一记钝器,敲在迟砚棠心口。
她没有再说话。
只是轻轻合上眼睛,眼角发涩。
她忽然想起,他们刚结婚那会儿,她半夜发烧,岑御琛还会一遍遍试温、喂药、握着她的手说别怕。
可现在,他们已经走到了连一丝耐心都没有的地步。
婚姻像是一座封闭的屋子,天花板上滴水不止,却没有人肯去修。
卧室里空气沉闷,阳光从落地窗照进来,斜斜落在床沿,把一地纷乱的衣物照得清晰刺眼。
迟砚棠从床上坐起来,头发有些凌乱,唇色泛白。她穿好衣服,脚步轻缓地下床。
水声响起,她接了一杯水,站在洗漱台前,拿出那瓶熟悉的药。瓶盖拧开的声音在静谧中格外清晰。她低头,倒出一粒药片,仰头一口吞下,动作冷静到麻木。
“你还真是毫不犹豫。”
岑御琛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门口,语气低沉,眼神复杂地盯着她。
迟砚棠抬眼看了他一眼,神色淡淡,把水杯放回原处:“副作用越来越大,我不想再频繁吃这个。”
“你可以跟我说……”
“说什么?”她打断他,眼神清澈却像蒙了一层霜,“让你睡之前先问我愿不愿意?”
她声音不高,却每一个字都像刀锋划过耳膜。
岑御琛眉头紧蹙,呼吸一窒:“是我一时气急,但你也不是第一次……”
“所以我该习惯?”她嗤笑一声,转身走出浴室,“你只要舒服就好,别管我吃不吃药,会不会难受。”
岑御琛沉默地站在原地,看着她瘦削的背影,心里一阵烦躁翻涌。他想开口,却说不出一句能让她留下来的话。
阳光越发炽热,屋子里却仿佛越来越冷。
迟砚棠拉开衣柜,开始换上干净的衣服。她的动作平稳而有序,仿佛这一切不过是日常生活里一个无聊的环节。
岑御琛看着她,喉咙动了动,终究没再说什么,转身离开了卧室。
陈妈把饭菜热好,一道道摆上桌,敲了敲楼梯栏杆的扶手,温声喊道:“先生、太太,吃饭了。”
迟砚棠从衣帽间出来时,已换上一套浅米色家居裙,脸上看不出情绪。她慢慢下楼,在餐桌前落座。
几分钟后,岑御琛也下来了,身上的西装已换成了居家的衬衣长裤,脸色仍然沉着。他坐在她对面,一言不发。
饭桌上气氛沉闷得像凝固的空气。
筷子碰到瓷盘的声音显得格外清晰,陈妈端了汤过来,看了看两人,又识趣地退回厨房。
岑御琛夹了几口菜,胃里却没滋没味。他忽然觉得陌生——明明是再熟悉不过的餐桌,对面也坐着他最熟悉的人,可他们之间仿佛隔着一整条街的距离。
他记得他们刚从大学毕业那年,自己顶着家里所有的压力,把她娶进家门。那时她穿着婚纱走向他,脸上是他最心动的笑容。他说“砚棠”,她就轻轻应一声,软软的像要化进他骨血里。
可现在的她,像是包裹着一层薄冰的壳,话少,笑少,看他的眼神也少了光。"

离婚后,前夫从7年前回来了全文免费
推荐指数:10分
迟砚棠岑御琛是现代言情《离婚后,前夫从7年前回来了》中出场的关键人物,“喵呜呜呜喵咪”是该书原创作者,环环相扣的剧情主要讲述的是:【清纯坚韧小白花X傲娇偏执豪门少爷|婚后失宠×离婚追妻|破镜重圆×失忆梗|双向虐恋×追妻火葬场|1v1】她是家境普通的清纯女孩,他是众星捧月的豪门少爷。大学时期,他在她最窘迫的时候出手相助,从此爱上了这个温柔倔强的女孩。他说:“我喜欢保护你的感觉。”婚后,她以为嫁给爱情,但一切都不尽如人意。直迟迟未孕,婆婆冷嘲热讽,他也在灯红酒绿中迷失。她一次次原谅,最终却在失望中选择放手。可离婚第二天,他车祸失忆,记忆回到两人热恋时:“棠棠,我们是不是要结婚了?”她以为这是上天最后的玩笑。他却像个执拗的少年,一遍遍追着她,一句句重复着当年的誓言——“棠棠,嫁给我,我这辈子都不想放开你。”直到后来记忆回归,才知最爱一直是她。“这次,我求你,再让我爱一次。”他捧着她的手,眼底是悔不当初的崩溃和柔情。走散的爱情,还能再找回来吗?...
第8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