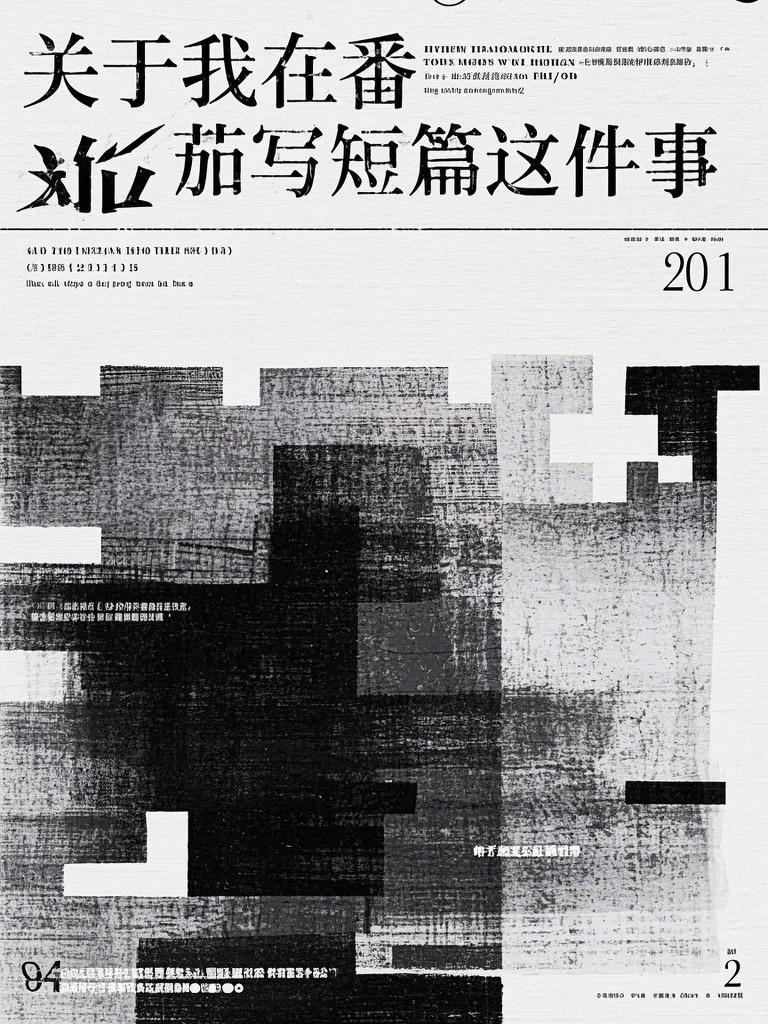“安哥儿,怎么了?可是学里又有人撕了你的书?”苏妈妈有些紧张的问道。
靳时安轻轻摇摇头,迟疑着说道:“不是。妈妈,刚才姨母把我叫过去,不知为何,她一直在哭,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苏妈妈心里咯噔一下,难道是太太出了什么事情?
另一边,靳岁欢还不知道这些事,她一直以为母亲和弟弟还在岳家好好住着,就是担心岳南笙那个毒妇会害死她们,她才肯老实待在周家。
但很快,她就知道了母亲的死讯。
周府后巷,冯妈妈送走了陈苏木,木然的回了院子里,关上了房门,坐在院子里一张竹椅上发怔。
她是岳家的家生子,从小伺候着岳家的人,长大后一直在夫人的院子里,跟单建中成亲后,两口子生下大儿子单正阳,一个管着外院的铺子,一个管着内院的吃食,日子还不错。
大小姐要嫁人了,夫人把他们一家子都陪送给大小姐做嫁妆,换了主子后,冯妈妈的日子便没有以前舒坦了。
大小姐性子乖张,脾气火爆,动不动就要发火,又同婆母不和,全靠着冯妈妈陪着笑脸帮着找补,有一回陈夫人气狠了,扔了木鱼梆子到岳南笙身上,是冯妈妈上前替她挡了,后背青紫了一块,疼了十来天才好。
别人看她是大少奶奶院里管事妈妈,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都交代了她去做,好似风光无限,内里的苦却只有冯妈妈知道。
冯妈妈不明白,大少奶奶明明也是大家子出身,夫人老爷万般疼爱,陪嫁丰厚,婆家也是官宦人家,家底殷实,这样从不缺钱的女子,为何会把钱看得那么重。
周家的月例银子都是有定数的,栖梧院院里自然也要跟着周家的规矩走。岳南笙虽觉得月例高了些,却也不得不照此安排。
陈夫人是个大方的,除了月例银子,别的院子里每月的脂粉、衣裳、针线……另外有银子采买,她觉得下人只有过得舒心,才能更好的服侍主子。
可岳南笙却不一样,除了月例银子外,拨给冯妈妈的银子屈指可数,她要拿着有限的银子,尽量维持着院里的体面,时常捉襟见肘,有时候甚至还要贴补一二。
去年秋分时,岳南笙胭脂铺子里有一批沉了很久的胭脂水粉,偏要抵了当季的胭脂钱,要冯妈妈发给丫鬟们使用。结果害得栖梧院的丫鬟脸上都起了红疙瘩,岳南笙却把责任推到了冯妈妈身上,冯妈妈只得自掏腰包,给众人看诊,又买了好的胭脂补上。
类似的事情不胜枚举。冯妈妈有苦难言。
就是这样,岳南笙还时常要查账,每每蹙眉问她:“这个月怎么又花了这么多钱?”
为了监督冯妈妈,岳南笙要求她记录下每一根针、每一寸线、每一块碎布头的去向,稍有“不明”就斥责她管理不善,话里话外意思都是冯妈妈贪墨了栖梧院的钱。
冯妈妈虽是奴仆,也是要脸面的,每每被气得脸色涨红,面对着主子却也不好说什么。
今年春上,新米还未下来,米价高涨,单建中掌管的米铺有一批陈米因保管不当霉坏了,他原本谈好了买家,准备卖给养猪的人家,谁知岳南笙知道后,不许他卖了,要掺进其他好的米里面一起卖。
单建中怕出了事,好说歹说劝着岳南笙,岳南笙却不肯听他的,执意要这么做。

表姐,我来接管你的人生了:全文+后续+结局
推荐指数:10分
《表姐,我来接管你的人生了:全文+后续+结局》中的人物岳南笙周复礼拥有超高的人气,收获不少粉丝。作为一部古代言情,“不如相思”创作的内容还是有趣的,不做作,以下是《表姐,我来接管你的人生了:全文+后续+结局》内容概括:【古言 架空 宅斗 虐渣 女非】文案一:靳岁欢只因长得有些像表姐,便被表姐夫妇设计囚禁代孕,宅院深深,母亲和弟弟被人拿捏,靳岁欢不得不认命。可后来,表姐她后悔了,她高估了人性。表姐夫也后悔了,他低估了女人。文案二:回乡守孝的探花郎宋引鸿最近很烦恼,总有个不知廉耻的妇人想要猥亵他,他实在厌恶那女人,可又觉得很奇怪,这女人怎么有两幅面孔,一会是舔不知耻的放荡人物,一会又变成冰清玉洁的清冷佳人。后来,他终于分辨出,面具之下,哪个才是真的她。...
第49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