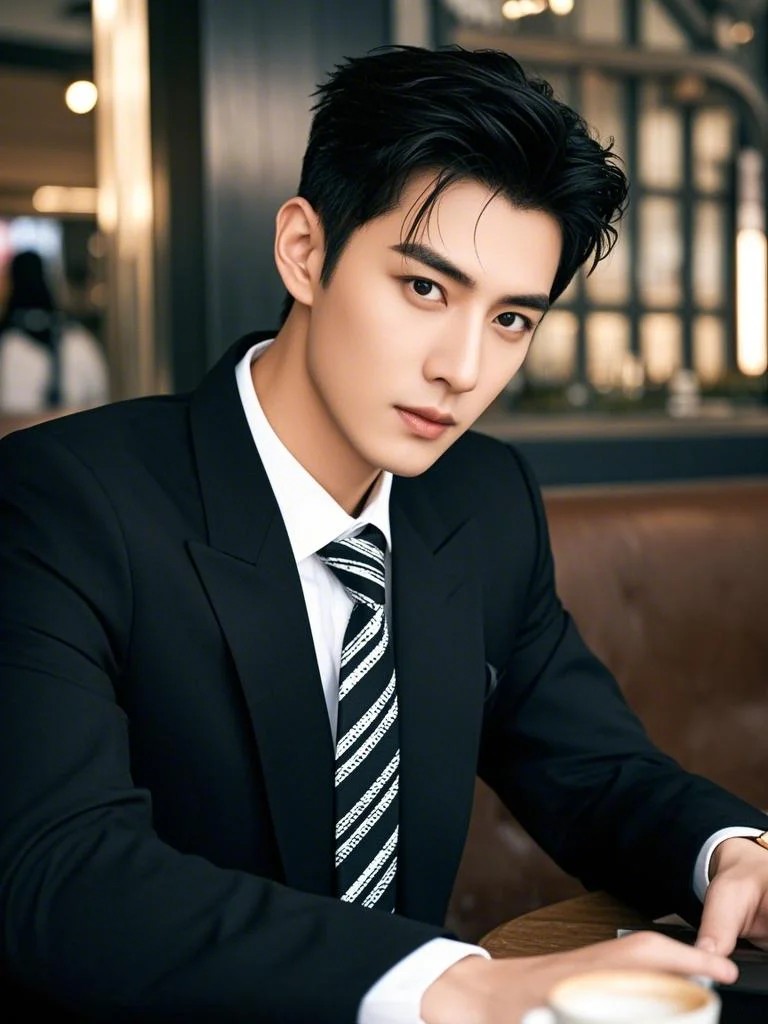孙子似懂非懂地点头,手里攥着刚得的小红花。
还有些年轻媳妇,聚在洗衣台边搓衣裳时,都透着羡慕。
“要是我家那口子也支持,我也想报个班,”一个媳妇说,“总在车间拧螺丝也不是长久事。”
另一个接话:“等她俩学出模样,咱也跟着试试。”
宋莹听说了张阿妹的酸言酸语,心里憋着股劲。
她学会计,刚开始看那些账本上的“借”和“贷”,就跟看天书似的。
她不怵,把家里买菜的钱、给林栋哲买文具的钱,都一笔一笔记在小本子上,对着课本琢磨:“这买菜花了五毛,是不是就跟车间领了材料似的,得记成花出去的?”
每天晚上,她就着台灯扒拉算盘,珠子打得噼里啪啦响。
有回算错了个数,急得直拍桌子,林武峰笑着帮她从头捋,她才算明白哪儿错了。
后来车间里算账,她算得又快又准,主任都夸她:“宋莹,你上夜大后,这脑子越来越灵了。”
黄玲学行政管理,也没闲着。
老师让写个通知,她琢磨来琢磨去,总觉得写得太啰嗦。
庄超英就拿学校里的通知给她看:“你看这上头,先说事儿,再说时间地点,清清楚楚。”
她就照着练,家里买煤、买家用,给孩子布置任务,她都自己写个条子记下来,练着把话说得明白利落。
俩人一有空就凑一块儿。
宋莹教黄玲认算盘上的数,黄玲帮宋莹顺顺作业里的句子。
有回张阿妹在巷口看见,撇着嘴说:“还真把自己当学生了。”
宋莹听见了,没吭声,就是手里的算盘打得更响了。
黄玲拉了拉她,笑着说:“咱接着练,让她看看。”
日子一天天过,宋莹的小本子记满了,黄玲写的条子攒了一沓。
巷子里的人都说:“这黄玲和宋莹,是真下功夫了。”
这天傍晚,黄玲正踩着缝纫机给图南补校服,忽然听见院门口传来熟悉的声音:“阿玲在家不?”
她掀帘出来,见黄父黄母拎着个布包袱站在院里,手里还提着一网兜苹果。
“爸!妈!你们咋这时候来了?”
黄玲又惊又喜,赶紧接过包袱。
上回八月底黄父黄母回常州本来说好领完工资就过来,结果因与相关部门交接退回剩余祖产的事,耽误了两个月。
黄母拍了拍她的手:“上个月你说你报了夜大,我跟你爸想着,你又上班又上课,还得带俩孩子,肯定忙不过来。家里如今没啥事了,就过来搭把手。”
黄父往屋里瞅了瞅:“超英呢?孩子呢?”
“超英去学校带晚自习了,图南和筱婷在隔壁栋哲家看电视呢。”
黄玲笑着往隔壁宋莹家方向走,“我这就去叫他们回来。”
黄母拉住她:“别叫了,让孩子们玩会儿。我跟你爸带来了红薯干,等会儿蒸上,给孩子们当零嘴。”
说着就往灶房钻,路过外间看到餐桌上堆着的课本,拿起翻了两页,“行政管理?这字儿写得真周正。”
黄玲脸一红:“瞎写的。”
“啥叫瞎写?”黄父坐在院里的小马扎上,“能静下心来学就好。我跟你妈来了,往后接送孩子、做饭这些事,我俩包了,你只管安心上课。”
正说着,宋莹端着一碗萝卜干,见了黄父黄母,笑着给二人打招呼:“叔!婶!你们来啦!”
黄母拉着宋莹的手:“宋莹,听说你跟阿玲一块儿上夜大,学会计?”
“嗯,刚开始学,还不太懂。”
宋莹挠挠头。
“不懂就问。”
黄父接话,“我年轻时候管过厂子,虽说跟现在的会计不一样,但总算沾点边,有啥简单的,你也能来问我。”

小巷人家:穿成庄超英后断舍离庄英萧艳全文免费
推荐指数:10分
古代言情《小巷人家:穿成庄超英后断舍离庄英萧艳全文免费》目前已经迎来尾声,本文是作者“翡冷翠的霓虹”的精选作品之一,主人公庄英萧艳的人设十分讨喜,主要内容讲述的是:38岁的庄英捏着银行卡时,手心还残留着十五年跑销售、干代驾的汗渍。这200万本是他买房的首付,是和老婆萧艳规划七年的婚房钥匙,却在签合同刷卡时,被告知余额不足。当他带着开车回家家途中,萧艳一句“我弟上周刚用那笔钱付了首付”如冰锥刺骨——所谓的救命钱,早已变成妻弟婚房的首付与新娘的彩礼三金。视频通话里,岳母数着彩礼单冷笑:“萧艳有出息就该帮衬弟弟,不回来喝喜酒就别认亲。”暴雨夜的高速路上,庄英眼前交替闪过萧艳的离婚短信、岳母数钱的指节、小舅子新房的红双喜。方向盘失控的刹那,他脑海里只剩一个念头:这被老婆原生家庭透支的人生,真可笑。再次睁眼,消毒水味换成了公共厨房的油烟气。他躺在八十年代苏州纺织厂筒子楼里,身上是打满补丁的的确良衬衫,镜中映出《小巷人家》里“孝庄”庄超英的脸——那个婚后仍把一半工资如数上交、被父母PUA,孝心外包,只知道窝里横,遇事委屈自己老婆孩子的高中数学老师“孝庄”。指尖划过裤袋里皱巴巴的工资条,又瞥见母亲正伸手要掏他的口袋。融合了双重记忆的庄英突然冷笑出声:这“冤大头”的人设他要亲手撕碎,被原生家庭算计的人生他早就不想干了!...
第41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