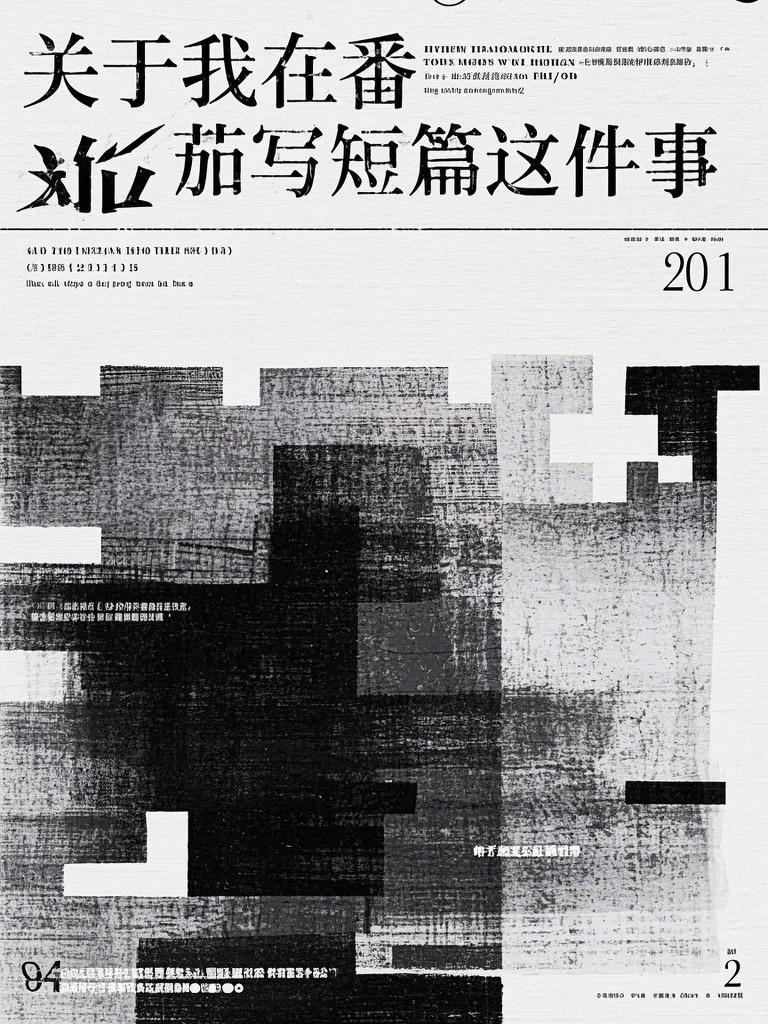“是啊,我疯了。”我看着他,眼泪终于毫无预兆地滚落下来,不是因为悲伤,而是因为极致的恨和绝望,“顾砚迟,我他妈就是疯了!被你逼疯的!你满意了?”
“满意?”他像是听到了什么极其荒谬的话,眼神阴鸷得能滴出水,“我满意什么?满意你像个疯子一样胡言乱语?满意你把自己搞成这副鬼样子?”
他烦躁地扯了扯领带,眼神扫过我苍白如纸的脸,扫过我手背上因为针头错位而渗出的血迹,最后落在我平坦的小腹上。
那眼神,复杂得难以形容。
有愤怒,有厌恶,似乎还有一丝……极快闪过的、连他自己都没察觉的痛楚?
但那点微不足道的情绪,瞬间就被更深的冷酷覆盖。
“够了!”他猛地打断病房里死寂的对峙,声音冰冷得不带一丝温度,“事已至此,多说无益。”
“这笔钱,足够你养好身体,重新开始。”他的语气恢复了那种高高在上的掌控感,仿佛一切又回到了他熟悉的轨道,“把身体养好,别再给我找麻烦。以后,我们两清。”
说完,他不再看我一眼,转身就走。
仿佛多停留一秒,都会沾染上晦气。
病房门在他身后“砰”地关上。
震得墙壁似乎都在轻颤。
那张轻飘飘的支票,落在我腿上。
上面的金额,后面跟着一串零。
普通人几辈子都挣不到的数字。
买断了一条命。
买断了五年的痴傻。
买断了我对他最后一点可笑的幻想。
我伸出颤抖的手,拿起那张支票。
指尖冰凉。
然后,我用尽全身力气,一点一点,把它撕得粉碎。
雪白的碎片,纷纷扬扬,洒落一地。
像一场迟来的、祭奠的雪。
两清?
顾砚迟。
我们之间,怎么可能两清?
你欠我的。
欠我孩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