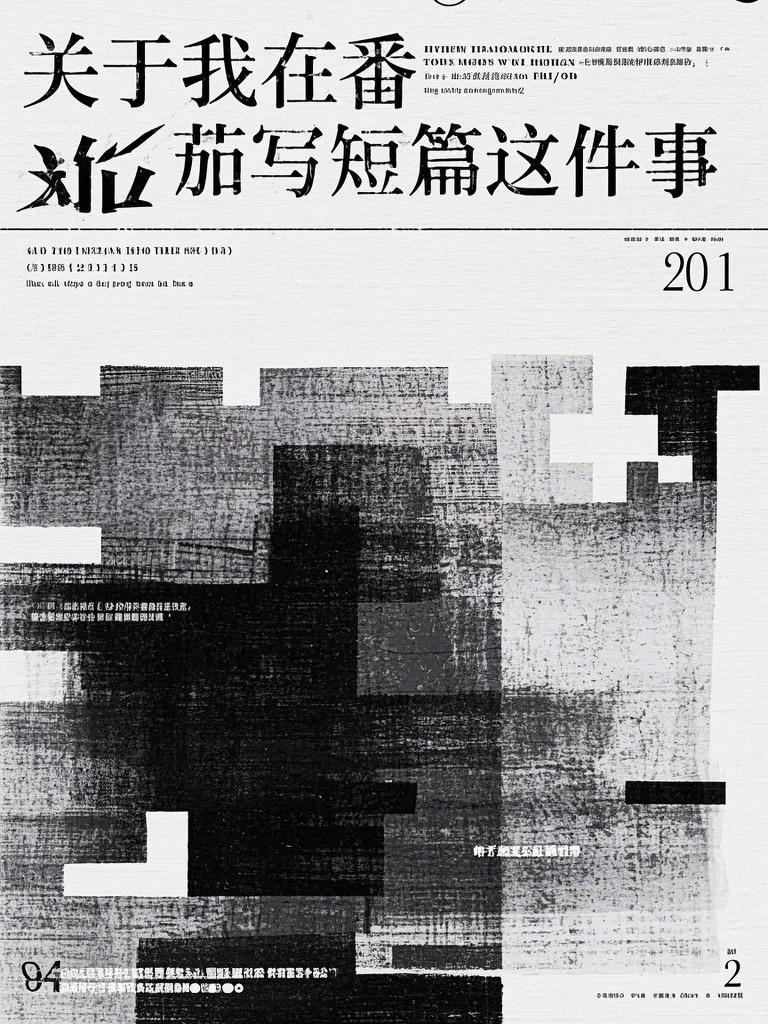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华母正蹲在灶台边,小心地用那珍贵的铜钱换来的几粒粗盐,搅拌着陶罐里翻滚的野菜粟米粥。小华佗也醒了,坐在草席上,小口喝着母亲喂来的温水。
就在这时,一阵沉稳而刻意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停在了篱笆院外。
不同于前几日那些乡邻的急切或试探,这脚步声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和缓慢的节奏。
华母搅拌粥的手猛地一僵,枯槁的脸上血色瞬间褪尽!她像被冻住一般,僵在原地,惊恐的目光死死钉在门口的方向。
秦凡的心也猛地一沉。他挣扎着坐直身体,布满血丝的眼睛锐利地看向那扇破旧的木门。来了!最不想面对的人,终究还是来了!
没有敲门,没有询问。
吱呀——
破旧的木门被一只枯瘦而有力的手,从外面缓缓推开。
门口的光线被一个佝偻的身影挡住。正是族老!他穿着那身略体面的深色麻布袍子,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浑浊的老眼如同冰冷的鹰隼,缓缓扫过昏暗的茅屋内部。目光在华母煞白的脸上停留片刻,又扫过靠在墙边、脸色苍白的秦凡,最后落在草席上懵懂睁眼的小华佗身上。
他身后,跟着两个同样穿着麻衣、面无表情的壮年汉子,是族里的后生,如同沉默的雕像。
空气仿佛凝固了,只剩下灶台上米粥翻滚的微弱咕嘟声。
族老的目光最终定格在华母身上,嘴角缓缓扯出一个极其刻板、没有丝毫温度的弧度,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沉甸甸的、如同磨盘碾压碎石般的威严和寒意:
“华家媳妇……听说……你们家……得了些……好本事?”
他的目光意有所指地扫过墙角那个空空如也、还残留着浓烈药味的石臼,以及地上散落的几缕粗麻线头。
华母枯槁的身体筛糠般抖起来,嘴唇哆嗦着,喉咙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扼住,一个字也发不出。巨大的恐惧让她几乎窒息,只能死死攥着手里那个豁了口的粗陶碗,指节因用力而泛白。
“族老……” 秦凡嘶哑的声音打破了死寂。他艰难地挪动了一下身体,牵扯得伤口一阵剧痛,声音里带着刻意的虚弱和一种不卑不亢的平静,“不知……您老……指的……是什么本事?”
族老的目光终于从华母身上移开,缓缓转向秦凡。那双浑浊的老眼里,审视的意味更浓,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阴鸷。他盯着秦凡苍白染血的脸,尤其是额角那块刺目的破布,嘴角那抹刻板的弧度似乎加深了些许。
“哦?大郎醒了?” 族老的声音听不出喜怒,反而带着一种长辈关怀般的虚伪温和,“头上的伤……可好些了?前些日子……庄里人心惶惶……闹了些误会……让你受惊了。” 他轻描淡写地将那晚的棍棒围殴和“烧死邪物”的嘶吼,归结为一场“误会”。
秦凡心中冷笑,面上却依旧平静:“托……托祖宗庇佑……捡回……一条命……” 他刻意强调了“祖宗”二字。
“祖宗庇佑?” 族老浑浊的老眼微微眯起,精光一闪即逝,“那自然是好的。只是……老夫今日来,是想问问……” 他话锋一转,声音陡然低沉下去,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探究,“你们这‘祖宗庇佑’的本事……可是从……外祖留下的……那几片烂竹简上……得来的?” 他的目光如同实质,死死锁住秦凡的眼睛,不放过任何一丝细微的变化。
烂竹简!他竟然直接点破了华母情急之下编造的谎言!而且用的是“烂竹简”这种轻蔑的称呼!
华母的身体猛地一颤,脸上最后一丝血色也消失了,眼中充满了极度的恐惧和绝望。完了!谎言被戳穿了!
巨大的压力如同冰冷的潮水瞬间淹没了秦凡!后脑的剧痛和眩晕感疯狂冲击着他的意识壁垒。他强忍着,心脏在胸腔里沉重地撞击着,几乎要破膛而出!族老显然已经暗中调查过!甚至可能从老叔公那里旁敲侧击过!他知道了那套说辞的漏洞!
怎么办?否认?对方显然有备而来!承认?那虚无的“竹简”根本经不起推敲!
电光火石间,一个极其大胆、甚至带着几分自毁倾向的念头,如同黑暗中劈下的闪电,猛地照亮了秦凡混乱的思绪!
不能躲!只能迎上去!用更离奇、更无法证伪的“事实”,堵住这悠悠之口!
秦凡缓缓抬起头,迎向族老那双如同鹰隼般审视的眼睛。他的脸上,非但没有被戳破谎言的慌乱,反而浮现出一种极其复杂、混杂着巨大痛苦、迷茫和一种近乎虔诚笃定的神情!仿佛在回忆某种深入骨髓、却又难以言说的经历。
“竹简……” 秦凡的声音变得异常飘忽,带着一种梦呓般的虚幻感,他的目光越过族老的头顶,投向门外灰蒙蒙的天空,仿佛在凝视着某个遥远的、不可知的存在,“是……也不是……”
这个模棱两可的回答,让族老枯瘦的眉头猛地蹙起,眼中闪过一丝不耐和更深的探究。"

我不是神医,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后续+结局
推荐指数:10分
《我不是神医,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内容精彩,“中二少年8号”写作功底很厉害,很多故事情节充满惊喜,秦凡华佗更是拥有超高的人气,总之这是一本很棒的作品,《我不是神医,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内容概括:三国,无系统,草根出身,多女角,神医加持,扮猪吃老虎。现代医生秦凡魂穿东汉,竟成神医华佗长兄华凡。开局以心肺复苏救活幼弟,却被愚民视为邪祟,惨遭棍棒濒死。家徒四壁中,他凭借超越时代的医术(麻杏石甘汤雏形、艾灸、鱼腥草消炎)与智慧,制作“避瘟囊”立足谯县,更以惊世手段折服曹操之父曹嵩,踏入洛阳漩涡。在帝都底层,他以“一文艾灸”救死扶伤,收服地头蛇疤爷,借势建立秘密基地“青囊义军”,招揽典韦、许褚、赵云,得郭嘉、戏志才辅佐。黄巾乱起,他率军解北海之围、扑灭常山瘟疫、阵斩张梁,立下赫赫战功,却遭董卓打压,强令解散义军,入京为闲散文官。洛阳已成董卓魔窟。秦凡隐忍入京,却于虎牢关外救下重伤的太平道圣女张宁与身陷灭门之灾的旷世才女蔡琰。他携红颜与结义兄弟,以微末议郎之身,周旋于董卓、吕布的虎视眈眈之下。焚华雄大营,救孙坚于绝境;虎牢关前,典韦一戟秒华雄,震慑诸侯;更亲率典、许、赵三英硬撼天下无双的吕布,以超凡医术与无双勇略,于汴水救曹操,于酸枣会盟扬名!...
第27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