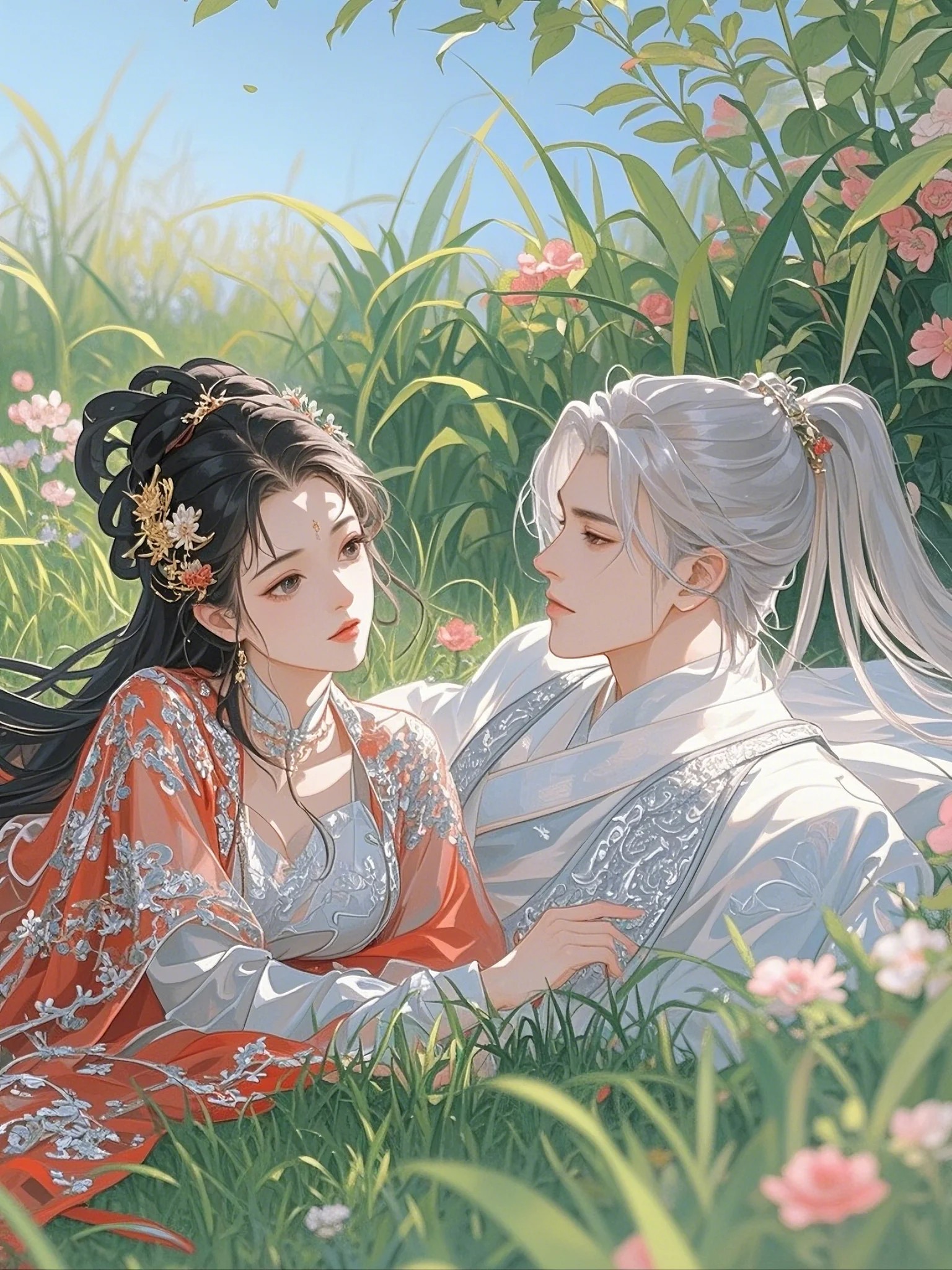他离开时的背影挺得笔直,谢婉枝看见他后腰处的衬衫皱了一小块,是她刚才挣扎时抓出来的。
走廊尽头传来打火机开合的声响,然后是烟草燃烧的苦涩气息飘来。
谢婉枝慢慢滑坐在地上。
膝盖碰到冰凉的地砖时,她才意识到自己一直在发抖。
转角处的烟头红光忽明忽暗,像只不肯离去的眼睛,在黑暗中静静注视着她。
…………
谢婉枝数着心电监护仪发出的电子音,第三十二个小时没有合眼。
走廊长椅的金属扶手硌着脊椎,消毒水浸泡过的空气钻进鼻腔,在喉管里凝成硬块。
护士第三次来劝她休息时,她发现自己在无意识地撕扯病历本边缘,纸屑雪花般堆在鞋尖旁。
“血压还在降。”医生推开ICU的门,白大褂下摆沾着碘伏痕迹,“家属要做好心理准备。”
眼前突然漫起黑雾,她抓住护士的手臂想站起来,膝盖却像被抽了骨头。
天花板上的荧光灯管开始扭曲变形,耳边传来金属推车急促的滚动声,有人托住她后脑勺时,她闻到熟悉的男士香水味。
醒来时躺在值班室的硬板床上,身上盖着男士西装外套。
周砚辞背对门口站在窗前,衬衫后襟有两道明显的褶皱。
听见动静转过身,手里端着的水杯水面还在晃动。
“喝点葡萄糖。”他声音比平时低,杯底在铁柜上磕出轻响,“你母亲...”
她猛地撑起身子,眩晕感立刻从太阳穴炸开。
周砚辞的手悬在半空,最终落在她肩上,触到又立即收回,仿佛被烫伤。
“醒了就去看她吧。”他转身时袖口掠过她脸颊,布料上有干涸的血渍,“刚恢复意识。”
母亲病床被摇起三十度,氧气管在耳后勒出红痕。
谢婉枝扑到床边时碰翻了输液架,药袋剧烈摇晃着投下晃动的阴影。
“怎么好端端出了车祸?”她握住母亲的手,无名指上的金戒指不见了,只留下圈苍白的压痕。
监护仪的滴答声突然变得很响。
母亲目光扫过她身后某处,嘴唇在氧气面罩下蠕动:“电话...砚辞他...”
玻璃窗外传来什么东西落地的闷响。
谢婉枝感到有冰锥沿着脊梁往上爬,母亲躲闪的眼神像把钝刀,一下下割着她胸腔里最软的部分。
“是不是他刺激你了?”她声音哑得自己都陌生。
母亲闭上眼,一滴泪滑进鬓角的白发里。
这个动作比任何回答都锋利,谢婉枝站起来时带翻了椅子,不锈钢腿砸在地砖上发出刺耳的哀鸣。"

京圈疯批大佬抢婚后跪求妹宝回头抖音
推荐指数:10分
小说《京圈疯批大佬抢婚后跪求妹宝回头》,相信已经有无数读者入坑了,此文中的代表人物分别是谢婉枝周砚辞,文章原创作者为“难欢而已”,故事无广告版讲述了:【伪兄妹\/疯批野痞混不吝京圈太子爷✖敢爱敢恨(有马甲)坚韧红玫瑰✖\/追妻火葬场\/极限拉扯\/上位者低头\/相爱相杀\/反转】“谢婉枝,你妈是贱人,你也一样。”周砚辞是个混不吝,他冷眼看着这个新来的继妹,眼底淬着毒。他早查清——是她母亲害得他母亲疯癫半生所以,他恶劣地勾着她的心,看着她小心翼翼讨好他,再狠狠碾碎她的天真那夜,她红着眼把自己献给他,却不知他根本滴酒未沾“想跟我在一起?”他捏着她的下巴冷笑,“行啊,但我们的关系,永远见不得光。”她甘愿做他见不得光的情人,却不知他早布好了一场毁灭性的报复两年后,他亲手送她一场断崖式分手,带新欢登门羞辱,逼疯她最爱的母亲,撞死他们养的狗狗,让她彻底坠入深渊以至于后来很长时间,谢婉枝在听到周砚辞三个字的时候,甚至会出现严重的戒断反应是啊,他也曾是她生命中的光…只不过现在,这束光被他亲手掐灭了后来,她浴血重生,挽着沈氏太子爷的手风光无限可婚礼当天,直升机轰鸣而至,周砚辞带着满身戾气闯进教堂“我在地狱里煎熬,你凭什么先逃?”他把她带到海岛足足21天,可她仍笑:“周先生我有丈夫了,您这种行为和您最恨当…有什么区别?”...
第61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