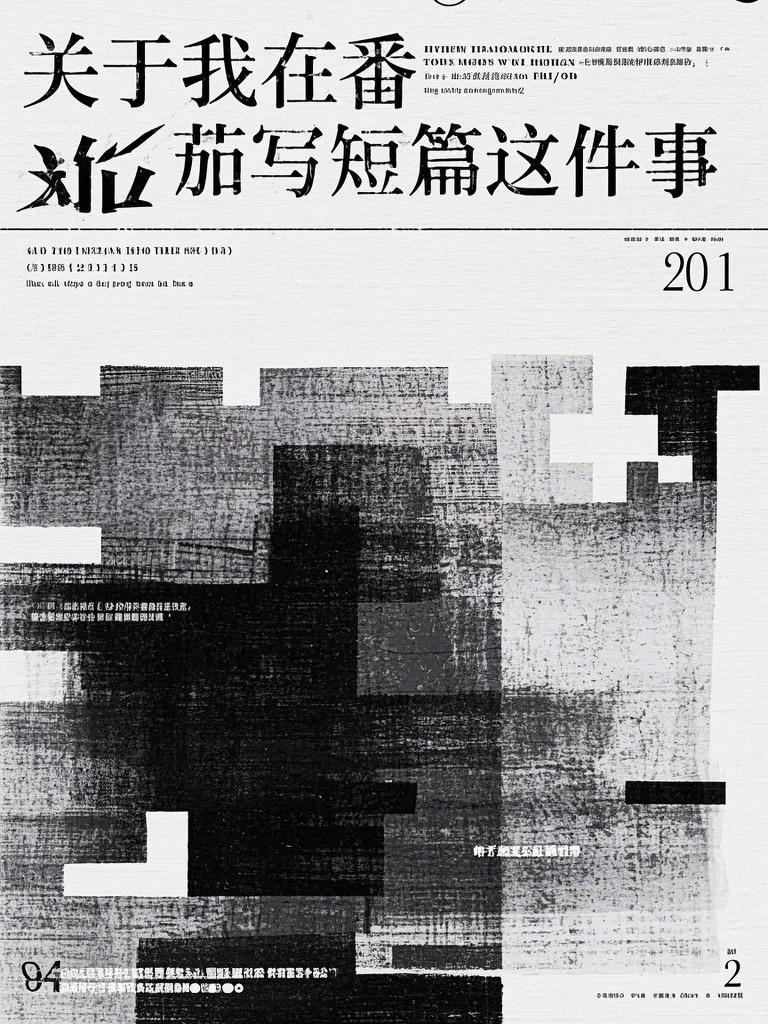“停车。”他轻声命令。
裕叔不多说,朝他递去一方柔软手帕。
陶景珩瞥一眼,像是嫌他老人家多管闲事,淡声拒绝:“不用。”
裕叔一点也不客气地收回了手帕。
司机迅速下车,为陶景珩打开车门,起身,下车的一瞬,扣上一粒西服扣子。
檀莞茜这会儿已经打完电话,只是经年沉积,被她死死关在心底的情绪,像是压抑已久的魔障,寻了丝缝隙就迫不及待钻出来,让她一时间收不住。
这种失控的情绪真的让人很讨厌。
她吸了吸鼻子,仰头想把眼泪逼回去,别在大马路上丢人。
逼到一半,鼻尖轻轻耸了耸,她好像在冷风中闻到一点熟悉的香味。
是沉香和雪松混合交缠的味道,很独特,让人想到雪山巅矗立的青松,冷傲而清冽。
她立马将仰了一半的头低回来,怀疑是自己的错觉,下意识四处张望。
直到身后传来皮鞋磕地的“嗒嗒”声,她猛地转身,滞住。
距离她还有两三步的人身形高大,笔直挺拔。穿很正式,很英伦的棕咖色西服,白色衬衫有很浅的条纹。浅灰色黑白条纹领带很规整地系着温莎结,西服口袋巾和领带同色。
檀莞茜总觉得他是欧洲某个皇家贵族培养出来的继承人,才每一次出现都这样精致贵重,叫人无端沉溺,挑不出错。
离得近了,那沉冷的香味愈发分明。
她仰头,愣愣看着面前的男人,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怀疑是自己情绪失控,白日做梦。
陶景珩与她保持绅士的社交距离,垂眸看她还挂在颊上的两滴泪,以及红红的眼眶和鼻尖。
像被雨淋湿了的山茶。
“怎么哭了?”他语调平淡地问,不含多余的情绪,更像是遇到熟人了,礼节性的询问。
偏偏让人觉得好像在被他关心。
檀莞茜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没头没尾地问一句:“你不冷吗?”
陶景珩默了一息,弯了点唇角,镜片后漆黑视线里荡漾出一点柔软:“不冷。”
而后抬手,抽出西服前襟里的口袋巾,在指尖展开,抵上她湿漉漉的脸颊,很轻柔地蹭了蹭:“又被人欺负了?”
檀莞茜眨眨眼睛,透过那方柔软的口袋巾感受到他指尖的温度,很温暖,很干燥。
让她想到夏天的云朵,落在脸上,应该也是这样的温度。
她咽了咽喉咙,诚实道:“不是,是开心。”
然后像终于反应过来一般,匆匆去接他的口袋巾:“景先生,抱歉,我自己来就好。”
陶景珩收了手,插进西裤口袋,属于他的口袋巾就落到她指尖,又擦干了她脸上的泪。
他像打量小动物般打量她乱糟糟,匆忙忙的动作,眼神浓淡得宜,不让人觉得冒犯。"

冠宠京华抖音
推荐指数:10分
古代言情《冠宠京华》,讲述主角檀莞茜陶景珩的甜蜜故事,作者“九绾”倾心编著中,主要讲述的是:【温柔沉稳年上daddyX清冷坚韧小白花|年龄差8|老房子着火|破镜重圆|追夫火葬场】初见陶景珩,檀莞茜就把人按在门上亲了,还硬拉着人睡了一晚。对方宽容大度,真的陪了她一晚。第二天醒来,她提着刀去找算计她的人算账,准备和人同归于尽。-回顾她的前半生,娱乐圈天降紫微星,一戏爆红,却惨遭封杀,属于她的奖项全部被撤。她以为这辈子也就这样了。谁曾想金牌编剧竟内定她当女主,王牌经纪人全程带飞。黑料都是误会,票房都是实力,绯闻都是姐的魅力。唯一出错的是她招惹了那个站在权力巅峰的男人。-明卓集团掌权人陶景珩,矜贵无双,雅致端方,从无绯闻。只有她知道这样如天上月,山巅雪的人也会眼尾泛红,不解又执着地追问:“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要分手?”她拍戏,他伴身旁。看她穿婚纱,对别的男人说爱语,只觉千万根针穿心而过。收工后,陶景珩将她死死按在墙上,崩溃至极只求一个答案。“茜茜,求你告诉我,你演爱我的那些日子里,有没有哪怕一秒,真的爱过我?”-他也不过是一个爱情囚徒。...
第58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