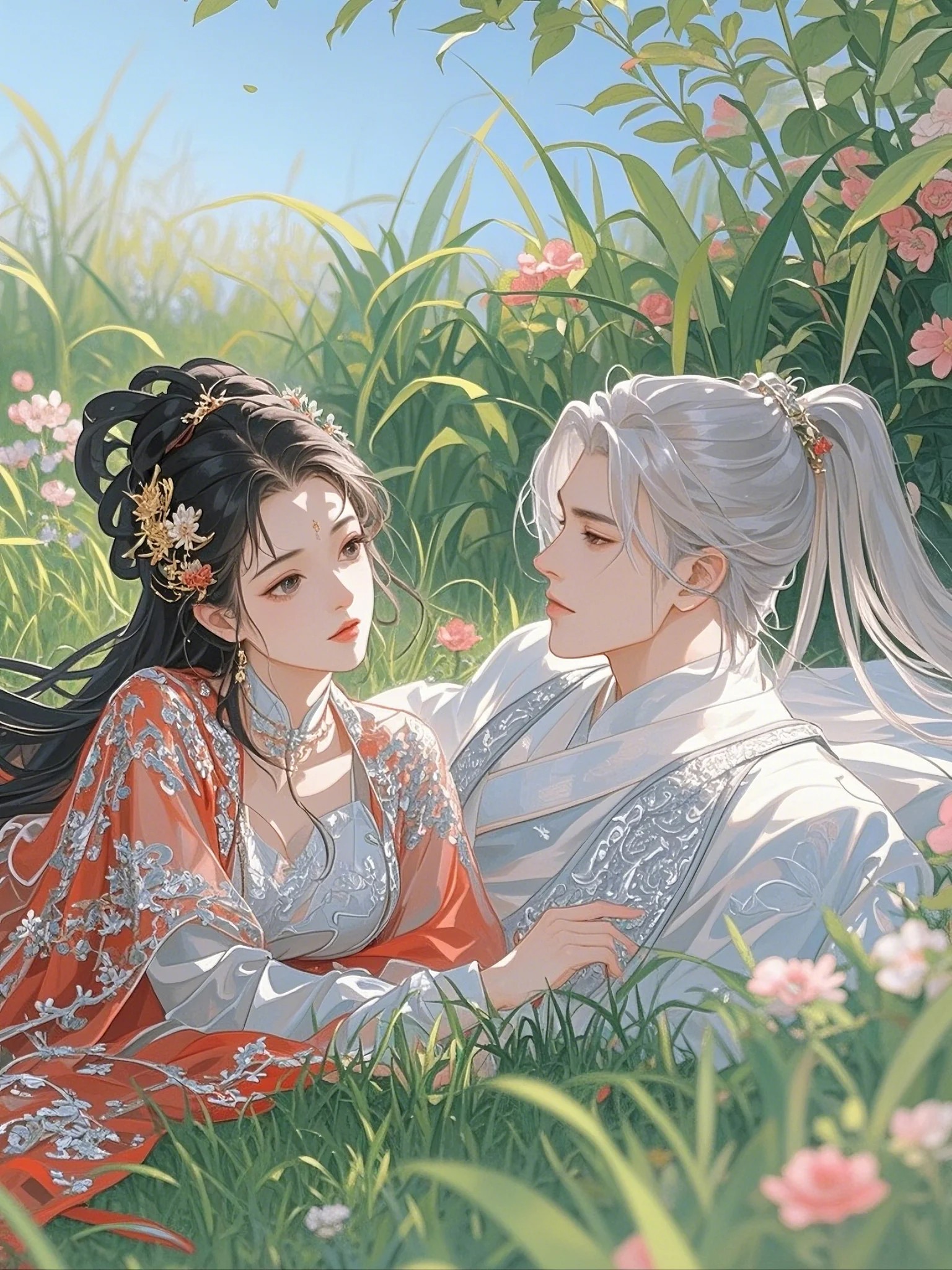台下有人窃窃私语,不懂刚才还尽显专业的许老师到底怎么了。
他却恍若未觉,哆嗦着嘴唇,颤声问周围的人,里面的标本是什么时候收入?
生前叫什么名字?
周围人不明所以,却还是如实回答。
他得到答案,像是失去了支撑自己站在这里的所有力气,猛然脱力跪了下来。
台上台下,一片哗然。
有人大喊着”许老师体力不支,讲座到此结束”,上前去搀扶他,却被他发疯般推开。
他抬起手,轻轻搭在玻璃罐上,对着里面浮沉的标本,喃喃念着什么。
我飘过去,终于听清了。
一遍又一遍,他只念着两个字:
“安然……安然……”
仿佛很久之前,他也曾一遍遍叫着这个名字,只为了那一句“安然无恙”。
许澈被强行抬走了。
我看着他的身影,心口莫名痛了下。
很奇怪,直到现在,我还是想不起来,他究竟是谁,
为什么会对着我的遗体情绪失控成那样。
可我还是跟了上去。
我看到他启动车子,疾驰到家,然后踉跄着上楼,从角落抱出一个大箱子。
箱子保存地极好,连一处磕碰都没有,只是上面落落厚厚一层灰,应该是许久都没有打开过。
他愣愣看了许久,终于打开了箱子——
里面是很多琐碎的东西,有一些滑稽可爱的冰箱贴,褪色的石膏娃娃。
而最里面,还有一个老旧的平安符。
他从里面翻出一个带锁的日记本,试了好几次,却都没能打开。
愣怔许久,他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颤着手,缓缓将数字拨到了“627”的位置。
“咔嗒”一声,锁扣打开,许澈的眼睛瞬间红了。
627,是什么?
日记本上明明写着安然的名字,可我却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许澈翻开日记,我也凑近去看。
看得出这本日记有些年头了,最初的字迹还很青涩,语句也很活泼。"

婚后五年,丈夫的同事怀孕找上门安然许澈无删减全文
推荐指数:10分
《婚后五年,丈夫的同事怀孕找上门》这部小说的主角是安然许澈,《婚后五年,丈夫的同事怀孕找上门》故事整的经典荡气回肠,属于现代言情下面是章节试读。主要讲的是:二十八岁生日那天,是我和老公结婚五周年纪念日。结束商务应酬后,将近午夜我才回到家。可客厅一片漆黑,没有任何活人生活的气息。我忽然觉得有些乏味,提前结束应酬,掐着点回来干嘛呢?可到底,还是有些不甘心。明明十年前的今天,他就站在我身侧,含笑的眼里装着的都是我。他在我耳边轻声说,自己报了医学院,以后一定会成为很厉害的医生。然后治好我的偏头痛。十年过去,他也早已成为脑外科精英,而我也如愿以偿,在商界风生水起。婚后第五年,他科室的女实习生大着肚子找上门来。我问他打算怎么解决。他却只说要离婚。...
第13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