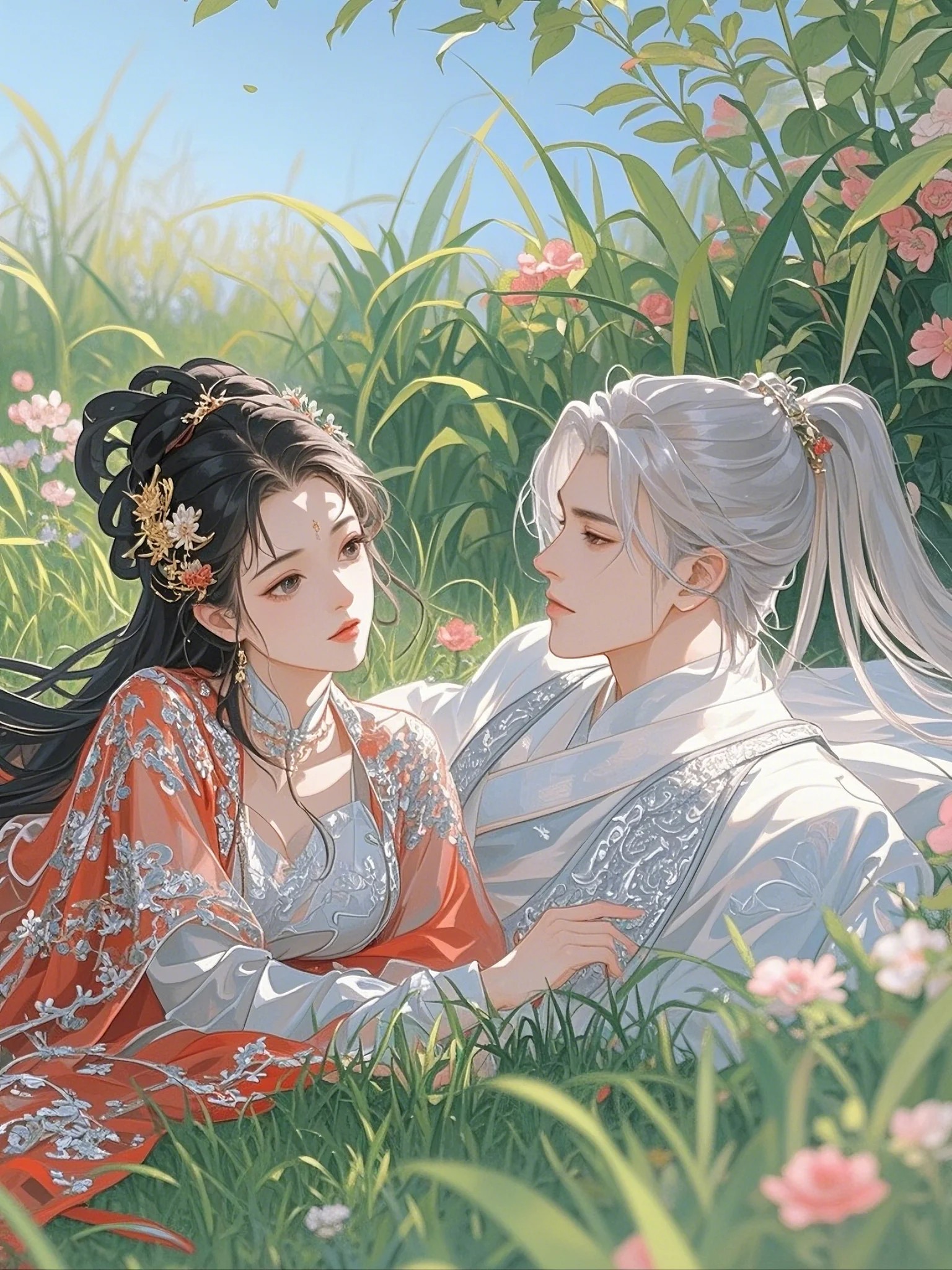第二天早上,我听见妈妈轻手轻脚出了门。
我偷偷跟出去,看见妈妈往县医院的方向走。
下雪天天气很暗,医院后门亮着盏昏黄的灯,几个面黄肌瘦的人蹲在墙根下排队。
穿白大褂的男人叼着烟喊:“O型的先进!”
妈妈赶紧举起胳膊。
我躲在梧桐树后面,看着妈妈蜷在长椅上。
护士把粗针头扎进她胳膊时,妈妈别过脸去,眼睛闭得紧紧的。
暗红的血顺着胶管流进玻璃瓶,一瓶、两瓶......妈妈的脸越来越白,像糊窗户的纸。
“四百毫升,十块钱。”
白大褂数出两张五元票子,“下次别空腹来,上回有个晕过去的。”
妈妈弯腰接过钱时,突然晃了晃。
她扶着墙慢慢蹲下,过了好一会儿才撑着膝盖站起来。
我跑回家钻进被窝假装睡觉。
妈妈回来时带着一身消毒水味,冰凉的手摸了摸我的额头。
"

亲父弃我十四年,病后求我捐骨髓最新热门小说
推荐指数:10分
网文大咖“此生长乐”最新创作上线的小说《亲父弃我十四年,病后求我捐骨髓》,是质量非常高的一部现代言情,招娣周志强是文里涉及到的关键人物,超爽情节主要讲述的是: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我爸爸有两个家。爸爸的儿子跟我同年出生。在我七岁那年,爸爸提出了离婚。我爸说如果妈妈不净身出户,他就把我争过去。现在可以到他们家照顾他儿子,长大了还能卖一笔彩礼钱。他洋洋得意的告诉妈妈,她没有工作,肯定争不赢他。为了拿到抚养权,妈妈选择净身出户。十年后,爸爸却又回来了。原来他得了......
第10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