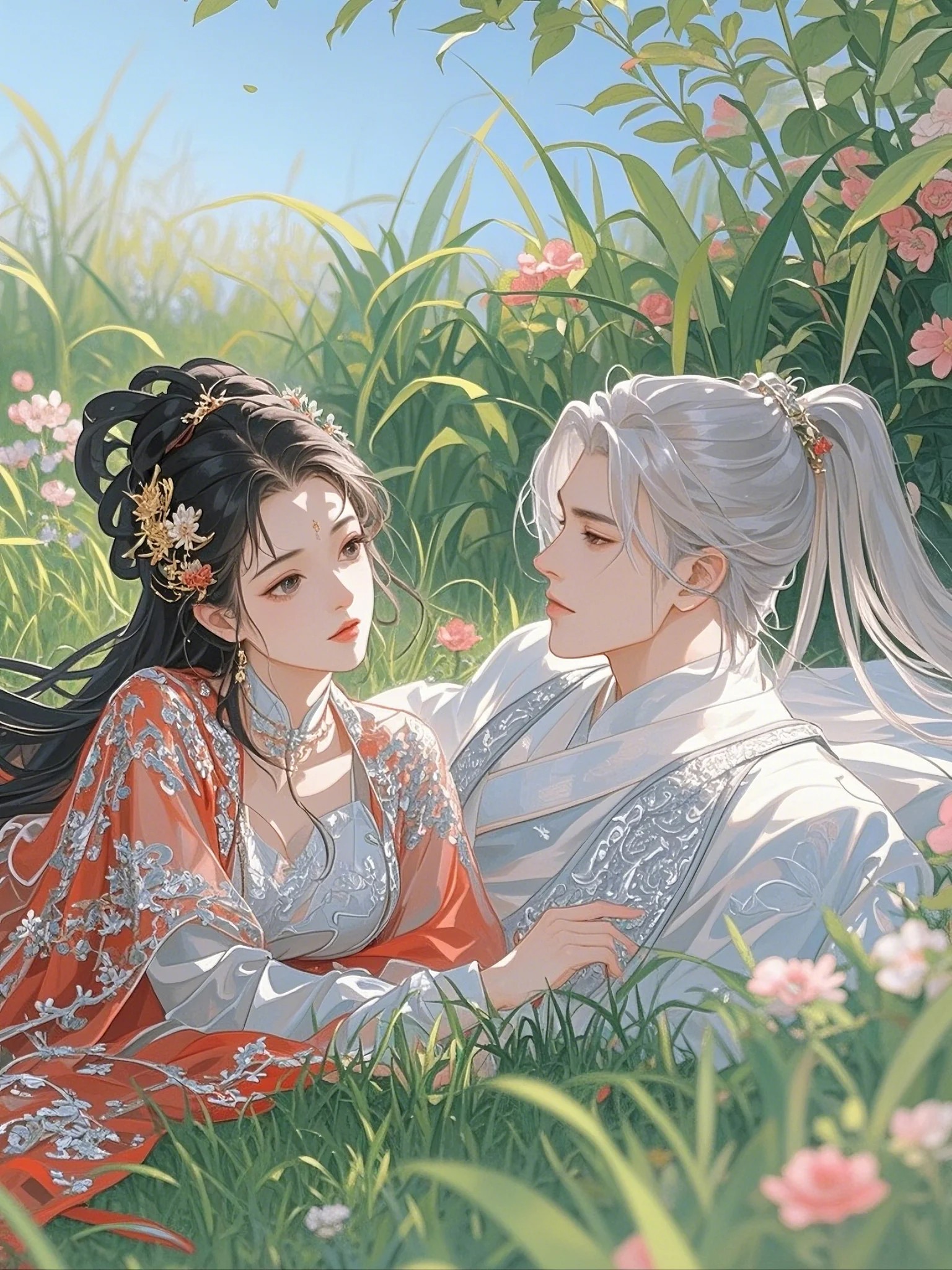房门一闭上,那些狂风暴雨顿时被拦截在外,室内中燃着两盏油灯,明亮又温暖。我身上湿透,大少爷在风口站了许久,也不遑多让,能看到他肩膀已经洇湿了一块。
我担忧道:「怎么办,不会发高热吧,要不我再去煮点姜汤给你。」
大少爷没应声,他开了衣柜,从中取出一套衣裳。
我见他要换衣裳,自觉背过身去,孰料肩上被人从后拍了一下,大少爷不容置疑道:「」换上。」
竟是给我的。
可我怎好再穿他的衣裳?
我刚想要推脱,冷不丁瞧见他唇上咬出的血印,瞬时就不敢再跟他犟了,跑到屏风后面,三两下换了衣裳,又另外取出一套,帮他换了,扶着他到床上趴下。
屋里能盖的东西都被我翻出来,盖到他身上。
可他身上实在太凉了,像三尺深潭,越往下,越寒气逼人。两个汤婆子,显得那么渺小,完全不够用。
我问:「大少爷,你冷吗?」
他说:「还好。」
这时他的嘴唇已经从白转青,我真的,这个世界上,怎么有这样嘴硬的人。
他嘴里究竟有没有实话?
还好我带了一瓶烈酒来。
我手忙脚乱倒了一杯酒,还没递过去想起他刚喝过药,只得作罢,这瓶烈酒算是白带。
于是我想了想,低低道了句:「大少爷,你可别怪我啊。」
大少爷神色茫然,显然有点没想明白他怪我什么。
下一秒,我从被窝里伸进去,放在了大少爷的屁股上。
手底下,大少爷的身子猛地一僵,然后慢慢紧绷绷起来,因为我已经隔着衣裳,顺着他的屁股开始一路往下揉。
怎么说呢……从前我们村里,冬天是有腌鱼的习俗的。
把盐搓在鱼身上,翻来覆去一顿揉,再挂起来风干。
现在这感觉也差不多。
我马不停蹄揉了两刻钟,手都酸了,才感觉手底下渐渐烫起来,再瞧趴着的大少爷,脸没那么白了,反而有点红。
那估计就是暖和了。
我问:「大少爷,除了冷,还疼吗,可好些了?」
他说:「好些了。」
但大少爷的话吧,我是真不敢信,伸手探了探他的额头,倒是没发热。
我说:「我还是出去请个大夫瞧瞧。」
大少爷说道:「你认得路?这么晚,又不是要命的病,不用折腾了。你且放心,我睡一觉就好了。」

十六娘未删节
推荐指数:10分
最具实力派作家“佚名”又一新作《十六娘》,受到广大书友的一致好评,该小说里的主要人物是珠儿剑如,小说简介:我被魏昭娶为正妻的时候,整个上京城都在笑。昔日眼高于顶的魏家大少爷,落魄凤凰不如鸡,最后只娶了一个烧火做饭的丫头为妻。后来魏昭功成名就,想嫁他的世家贵女多于过江之鲫。我约了京城有名的媒婆,打算给他纳两门贵妾。临了却被本该在扬州办事的魏昭堵在家门口。他风尘仆仆,气得连身子都在颤。你今日敢出得这个门试试...
第15章